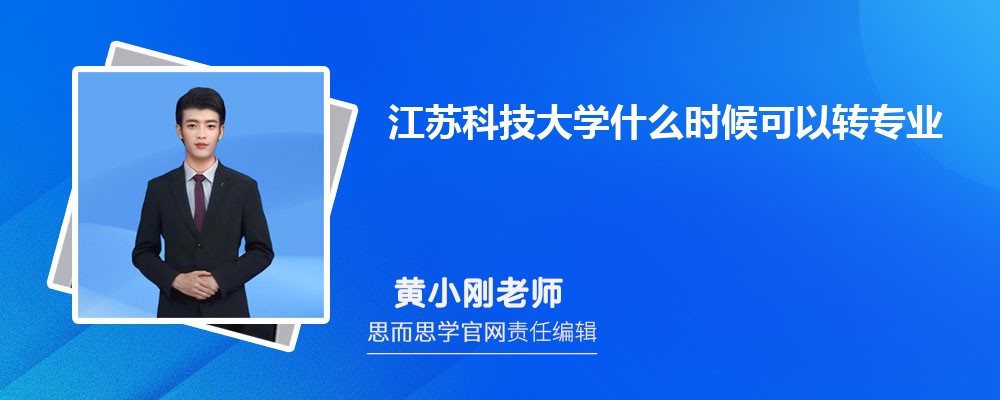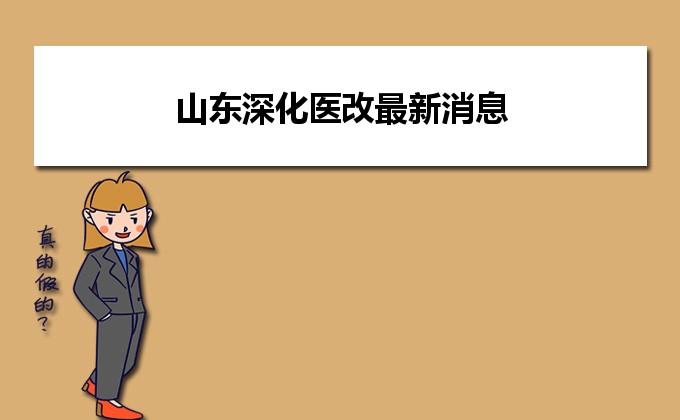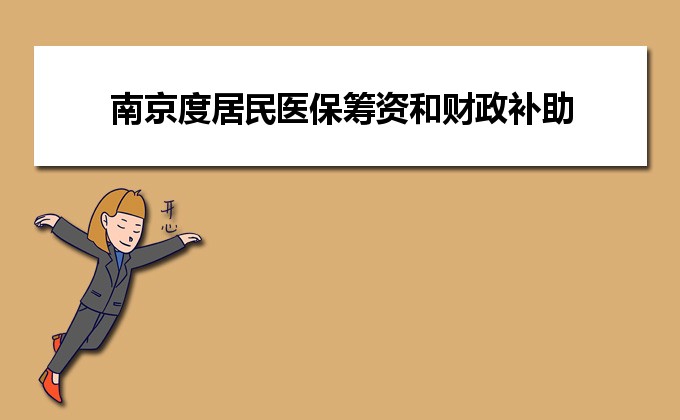農村醫改百年:“中國模式”震撼世界
國農村醫改:民國醫療全靠自費 江蘇首開融資先河
醫療改革一直是民眾關心的話題,而占中國總人口數過半的農村醫改百年歷程,不僅給世界提供了獨一無二的范例,也為未來中國醫改提供了寶貴經驗。本策劃內容摘自王紹光著《中國 治道》,人民大學出版社。
回顧中國農村醫改:民國醫療全靠自費 江蘇首開融資先河
20世紀初,大約85%以上的中國人居住在鄉下,那里的醫療衛生狀況相當原始。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其改造農村醫療狀況的規劃看似雄心勃勃。1934年衛生署頒行《縣衛生行政方案》,規定縣設衛生院,區設衛生所,每村配置衛生員;1937年3月,衛生署進一步公布了《縣衛生行政實施辦法綱要》。40年代初,國民黨五屆八中全會通過了《實施公醫制度以保證全民健康案》,聲稱“全民健康完全由政府負責”,“醫療衛生事業完全由國家經營,所需經費均由國庫或地方自治經費項下支給,全國民眾都有無條件享受之權利”。其后,衛生署頒布政令,擺出在全國推行公醫制度的架勢;連《中華民國憲法》第157條也明文規定,“為增進民族健康,應普遍推行衛生保健事業及公醫制度”。
雖然,政府的公文規定看似天花亂墜,而實際上,它從沒有把衛生事業當作一件大事。在“黃金十年”最好的1936年,國民政府對衛生的投入僅占政府全部財政支出的0.7%。無怪乎,鄉村衛生機構依然寥若晨星。直到1947 年,全國農村只有1397家縣衛生院,18家縣衛生所,352家區衛生分院,783家鄉鎮衛生所,醫師2569人,護士3530人,助產士1469人,檢疫人員1755人,病床11226張。 即使這區區1400余家縣鄉兩級衛生機構,也面臨嚴重的經費短缺問題。 至于規劃中的村衛生員,更是不見蹤影。 相對四億多農村居民的醫療保健需求而言,這種完全由國家財政融資、由國家經營的公醫制度不過是杯水車薪而已。在資源短缺的背景下,完全由國家財政融資為4億多農村居民建立公醫制度無異是癡人說夢。
實際上,在整個民國時期,個人付費是中國廣大農村唯一的醫療融資方式。由于農民普遍貧窮,負擔不起醫療費,他們得了病,根本不敢去看醫生;即使湊得出錢來,也很難找到醫生。 例如,創造出著名“定縣模式”的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畢業生陳志潛注意到,在離北京不過200余公里、靠近平漢鐵路的河北省定縣,40萬居民中,沒有一名西醫;在全部472個村莊中,有220 個村完全沒有任何醫生和醫療設備;在其它252 個村,每村也只有一個沒有經過任何正規培訓的自封的中醫;定縣病死人數中有三分之一沒有經過任何醫藥治療。
倒是在中國最富庶的江蘇省,1936 年2 月,由省立教育學院主辦的無錫惠北實驗區在小園里村進行了鄉村醫療融資實驗,其主要內容是每人每年繳納3 角錢的保健費,換取全年享受的免費醫療、注射預防針和種牛痘等權利,與后來的農村合作醫療有些相似。不過,該村很小,只有25 戶,137 口人。如果僅靠村民繳付保健費,總共每年只能融資41.1元。在這么小的范圍內靠這么點錢分攤健康風險,是否可行?該實驗有沒有外來基金資助?可惜唯一提到這項實驗的文章對此語焉不詳, 可見其生命力與影響力十分有限。
由于絕大多數人的健康沒有保障,解放前,中國的嬰兒死亡率高達250‰, 人均預期壽命則只有35歲左右,相當于美國1780年代的水平。
農村醫療差毛澤東震怒 一年四批衛生部
毛澤東在1945年指出:“所謂國民衛生,離開了三億六千萬農民,豈非大半成了空話?” 至于如何解決廣大農民的醫療衛生問題,那時共產黨只有一個粗略的思路,既是走合作的道路。毛澤東指出,“目前我們在經濟上組織群眾的最重要形式,就是合作社”;他認為,“這是人民群眾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窮苦變富裕的必由之路”。 在延安時期,各種形式的合作社已經出現,包括生產合作、消費合作、運輸合作、信用合作等。在這個背景下,陜甘寧邊區也出現了醫藥合作社。
最早的醫藥合作社被叫做“保健藥社”,籌建于1938年,由陜甘寧邊區政府民政廳領導,由西北局保健委員會和民政廳共同投資。除了總社之外,保健藥社還在延川、清澗、綏德、吳堡等20個市、縣設立了26處分社。這種藥社是一個醫療服務機構,實行制藥(主要是中草藥)、看病、賣藥三位一體的運行模式。雖然,它們對抗日軍人家屬實行九折優惠,對災民實行免費治療、免費吃藥,但主要還是靠個人付費。1944年,延安等地爆發傷寒、回歸熱等流行病。為了滿足廣大群眾的醫療要求,邊區政府委托當時的商業銷售機構—大眾合作社代辦成立了“衛生合作社”。衛生合作社總社設在延安,各縣、鄉設43個分社,其資金主要由大眾合作社與保健藥社籌集,并吸收民間團體及私人股金。與保健藥社一樣,衛生合作社也是醫療服務機構,雖然收費低廉,但還是要求個人付費。簡而言之,在新中國建立以前,合作的理念已進入醫療領域,但醫療融資方面的合作仍付之闕如。
新中國建立后,在1950 年8月召開的第一屆全國衛生工作會議確定了醫療衛生工作方針,其中第一條就是“面向工農兵”。到1952年底,全國縣級衛生機構已從1949年的1400余所增加至2123所,遍及全國90%以上的地區。在基層鄉村,政府的主要策略是鼓勵個體中西醫組建了聯合診所,為農民提供醫療服務。但直到1955年前,中國農村基本上實行的還是自費醫療制度;在醫療融資方面,沒有明顯變化。不過,農村醫療衛生方面需要合作的理念開始萌芽了。
1955年席卷中國農村的合作化高潮對發展提供醫療服務的農村基層衛生組織是個極大的促進。在其后短短2-3年的時間里,全國5萬多個鄉鎮都設立了聯合診所或區衛生所,多數農業合作社也都設有衛生室(站),配備有不脫產的衛生員、接生員, 為提出“農村衛生工作網”的概念奠定了基礎。 更重要的是,農業合作化成為合作醫療的催化劑:生產、資金、農具、技術上的互助合作啟發農民把互助合作擴大到醫療融資領域。張自寬的觀察可謂一語破的:“沒有農業合作化運動就不會有農村的合作醫療運動”。
1960年2月2日,*向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轉發衛生部的報告及其附件,并要求各地參照執行,但并沒有馬上引起各地政府足夠重視。 據毛澤東了解,“大多數省、市、區黨委第一書記沒有看這樣一個很重要而又寫得很好的文件,也沒有發到各級黨委黨組和人民公社去”。為此,他于3月16日為中央起草了《關于衛生工作的指示》,強調“中央現在提醒同志們,要重視這個問題”,“各省、市、地、縣、社要由黨委第一書記掛帥,各級黨委專管書記和有關部門黨組書記也要在黨委第一書記領導之下掛起帥來;立即將中央二月二日批示的文件發下去,直到人民公社”。 最高領袖的直接干預有力地促進了農村合作醫療在全國范圍的推廣。從此,集體保健醫療便成為中國農村的一項基本制度,無論是地處江南魚米之鄉的浙江, 還是遠在西北邊陲的新疆都不例外。 根據長期追蹤研究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安徽醫科大學衛生管理學院估算,全國行政村(生產大隊) 舉辦合作醫療的比重,1958年為10%,1960年為32%,1962年上升到46%。
同樣是在大躍進運動中,農村衛生服務提供體系得到進一步發展。縣醫院得到進一步加強;人民公社將國家舉辦的區衛生所和農業社的保健站整合為公社衛生院;生產大隊把聯合診所和村保健站變成大隊衛生室,生產小隊配“三員”(保健員、接生員和保育員),形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農村醫療衛生體系。
“據1964年統計:在衛生技術人員分布上,高級衛生技術人員69%在城市,31%在農村(縣和縣以下),其中在縣以下的僅占10%。中級衛生技術人員城市占57%,農村占43%,其中在縣以下的僅占27%。中醫則大多數在農村。農村的中西醫不僅按人口平均的比例大大低于城市,而且多數人的技術水平很低。在經費使用上,全年衛生事業費9.3億元中,用于公費醫療的2.8億元,占30%,用于農村的2.5億元,占27%,其中用于縣以下的僅占16%。這就是說,用于830萬享受公費醫療的人員的經費,比用于5億多農民的還多”。這種局面讓中共最高當局十分不滿。1965年5月26日,在同衛生部負責人崔義田、史書翰、計蘇華等談話時,劉少奇便指出:“現在的醫藥衛生工作只是面向一億左右的城市人口,全國70%的醫務人員是集中在城市,占五億多人口的農村中醫務人員和藥品都很少,為了解決衛生工作面向農村,藥品供應要研究,如何把供應點深入農村”。 毛澤東更是對此感到震怒,并在一年內第四次對衛生部作出嚴厲批評。1965年6月26日,在同他身邊的醫務人員談話時,毛澤東斥責“衛生部的工作只給全國人口的15%工作,而且這15%中主要還是老爺。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院,二無藥。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老爺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并號召“把醫療衛生的重點放到農村去”。這就是著名的“六二六指示”。 其后,7月17日,劉少奇聽取了衛生部負責人錢信忠、張凱、賀彪、郭子化、崔義田、史書翰等關于醫務工作如何為農村服務問題的匯報。 毛澤東又于7月19日和8月2日兩次與衛生部負責人談話,主要談農村衛生工作。8月份,中央政治局還專門開會討論了衛生工作。 中共最高*如此密集地議論農村醫療衛生工作,是空前絕后的。
有些人想當然地斷定,毛澤東的“六二六指示”“使1962年后幾乎處于停頓狀態的合作醫療制度出現了回升發展的重要契機”, “激起了全國上下對農村醫療衛生工作的極大重視,在50年代中期出現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由此推開”。 其實不然。雖然1965年前后毛澤東及其他中央*對農村醫療衛生表現出前所未有的關注,但他們的關注點集中在為農民提供醫療服務和為農村培養三種衛生人員上;而組織巡回醫療隊到農村去是逐步實現這兩個目標的關鍵。巡回醫療隊為農民治病并不是完全免費,而是“應按當地合理收費標準收取費用”。如果農民交不起醫藥費怎么辦?當時的做法是,“貧下中農出不起醫藥費的可以減免。減免費用,應當首先在社、隊公益金中解決。社、隊公益金中解決不了的,經過工作團審批,在工作團掌握的社會救濟費中解決;非重點社教地區,由民政部門掌握的社會救濟款內開支”。換句話說,毛澤東“六二六指示”并沒有給農村醫療融資的格局帶來多大變化,盡管大規模派遣城市巡回醫療隊,大規模培訓不脫產、半脫產的農村基礎衛生員,兩者都有助于降低農村醫療衛生的成本,為普及醫療融資合作鋪平了道路。
中國醫療模式受聯合國肯定:平均國民年齡從35飆升到68歲
合作醫療真正在全國農村得以普及是1969年以后的事。1968年7月底,毛澤東派工人宣傳隊進駐各大專院校,它標志著文革大規模群眾運動階段的終結。與此同時,針對當時宣傳工作中出現的“假、大、空”現象,毛澤東作出了“典型宜多,綜合宜少”的指示,提出要用先進的典型,來推動全國的各項工作。
醫療融資方面的合作醫療是中國農村初級衛生保健體系“三大法寶”中最關鍵的法寶。有了它,縣鄉村三級醫療衛生網和赤腳醫生才能實現低成本、廣覆蓋的效果;沒有它,即使不缺醫、不少藥,也會出現看不起病的問題。七十年代,中國還不富裕,但隨著合作醫療的普遍建立,赤腳醫生和三級衛生網充分發揮了各自的優勢,有效地為廣大農村居民提供了基本的醫療衛生保障,使中國人民的健康指標大幅改善,平均預期壽命從解放前的35歲增加到了1980年的68歲,嬰兒死亡率也從解放前的約250‰減少到1980年的50‰以下。當時中國醫療衛生服務的公平性和可及性受到了聯合國婦女兒童基金會、世界衛生組織和世界銀行的高度贊譽,例如世界銀行的《1993 年世界發展報告: 投資與健康》稱中國當年在醫療保障方面取得的成就在低收入國家是“獨一無二”的(a unique achievement for a low-income developing country)。 中國當時的低成本、廣覆蓋的模式也在1978年的阿拉木圖會議上受到推崇,成為世界衛生組織在全球范圍內推廣初級衛生服務運動的樣板。
回顧毛澤東時代農村醫療狀況的變遷,它從無醫無藥走到缺醫少藥,最后找到了合作醫療這條低成本、廣覆蓋的途徑。在這個過程中,各地的實踐起了巨大的作用。 文革中一度盛傳,上海川沙縣的赤腳醫生和湖北長陽縣的合作醫療都是“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抓的點”。實際上,它們都是實踐在先,抓點在后。群眾的實踐為決策者提供了靈感,是政策演變的動力源。
1976年9月,毛澤東辭世;1977年8月,中共第11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宣布文革結束。當時,沒有任何人預見到合作醫療將會迅速衰落。恰恰相反,1978年3月5日五屆全國人一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次將“合作醫療”寫入憲法,列為國家為保證勞動者健康權利需要逐步發展的事業。當年12月,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拉開了改革的序幕。一年以后,1979年12月15日, 衛生部、農業部、財政部、國家醫藥管理總局、全國供銷合作總社聯合發布了《農村合作醫療章程( 試行草案)》。這是政府部門第一次發布關于農村合作醫療的正式法規性文件,標志著合作醫療的制度化。它將合作醫療定義為“人民公社社員依靠集體力量,在自愿互助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一種性質的醫療制度,是社員群眾的集體福利事業”,并承諾“根據憲法的規定,國家積極支持、發展合作醫療事業,使醫療衛生工 作更好地為保護人民公社社員身體健康,發展農業生產服務”。 在此前后,*主席華國鋒、副主席葉劍英都明確要求,“鞏固和發展農村合作醫療事業”。
改革開放后一度遍布全國的合作醫療迅速偃旗息鼓,最重要的原因是合作醫療所依托的經濟基礎發生了變化。八十年代擔任衛生部長的錢信忠說的一針見血:“沒有農業合作化運動就不會有農村的合作醫療”。這句話不僅揭示了合作醫療興起的條件,也點明了合作醫療存活的條件。只有在集體經濟的制度環境下,合作醫療的資金才能直接從集體經濟中提留,保證了籌資途徑暢通。七十年代末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尤其是人民公社解體以后,在廣大農村,家庭成為農業生產經營的基本單位,除少數地區有集體所有的鄉鎮企業外,大部分鄉村的集體經濟十分薄弱,甚至完全不存在。在這種情況下,除非形成新的醫療融資渠道,用提留集體公益金的方式來扶持合作醫療,在很多地方已經失去了可行性。
八十年代前期,有些文件甚至千方百計試圖避免使用“合作醫療”這四個字,而是代之以其它名詞,如“集資醫療”。由于中央態度曖昧,各級領導對扶持合作醫療也沒有興趣。用農民的話說,“上面不喊了,中間不管了,下邊就散了”。安徽醫大的調查也表明,各地領導干部的態度是決定合作醫療能否堅持的關鍵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