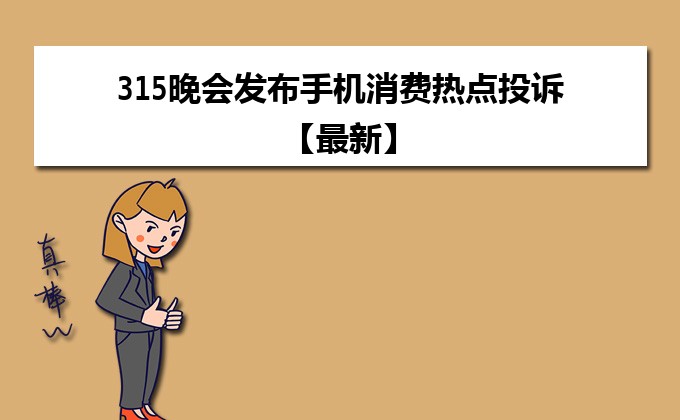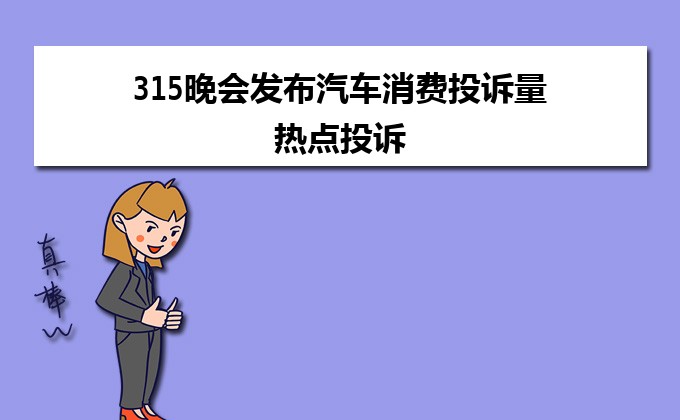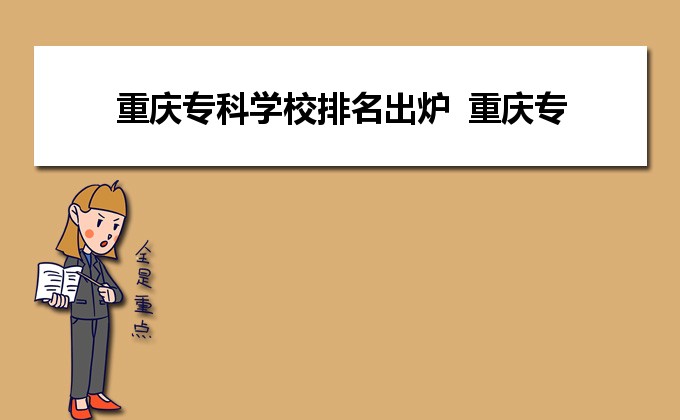一、重大歷史進步
網絡安全不是今天才重要,網絡安全立法也不是今天才迫切。十二年前的中央文件曾罕見地以書名號明確了立法任務,可見決心之巨。只是網絡安全立法之路實在艱辛,時國務院信息辦審時度勢,由信息安全條例角度入手,并連續數年推動其列入國務院法制辦二類立法計劃,之后未能再進一步。2008年后,國務院信息辦職能整體劃轉至工業和信息化部,有關方面意識到制定條例未必就比人大立法容易,且國務院行政法規無力調整現行上位法的法律規定,遂決定返回制定信息安全法。然而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頗多領域亟待立法,國家立法資源有限,每個部門允許提出的立法建議屈指可數。工業和信息化部既要考慮信息化立法,還要考慮工業立法,一半指標已不得用,而信息化方向還有一部歷史更為悠久的電信法望眼欲穿,信息安全法終究連個隊都沒排上。期間,人大建議、政協提案不計其數,社會公眾翹首以盼,均無果。
此次草案公開征求意見,表明這項工作進入了實質性立法程序,這是一個重大歷史進步。歡欣鼓舞之所在,不是因為草案具體內容,而源于征求意見本身的象征意義。時至今日,我們對網絡安全立法不是搞清楚、看明白了,而是問題更多、更復雜了,很多觀點分歧可能更大了,網絡安全立法難度不降反升,但突破恰恰在此時。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成立后,中央領導同志英明決策,切實將網絡安全提升到了國家安全和發展的高度,不但作出“網絡強國”的全局戰略部署,更扎實推進各項工作取得積極進展。網絡安全宣傳周、網絡空間安全一級學科等,無一不歷經多年論證而蹉跎,今朝方開花結果。
誠然,網絡安全立法工作十分艱巨,草案肯定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今天的一小步,是國家網絡安全工作的一大步。我們應該寬容它、呵護它,使其不斷成熟、更加科學,成長為護佑國家網絡安全和信息化發展的參天大樹。
二、彰顯國家意志,確立基本原則
草案在“總則”和“網絡安全戰略、規劃與促進”部分提出的宣示性條款遠較其他法律為多,還設立一條倡導性條款(即“倡導誠實守信、健康文明的網絡行為”)。作為我國網絡安全的基本法,這些“軟性”法律規定確有必要,其意在于宣示國家網絡安全工作的基本原則,明確建設網絡安全保障體系的主要舉措,從而為整體推進保障體系建設提供法律依據。
一是堅持網絡安全和信息化發展并重原則。網絡安全和信息化是一體之兩翼,驅動之雙輪,要堅持以安全保發展、以發展促安全,不能簡單地通過不上網、不共享、不互聯互通來保安全,或者片面強調建專網。要努力實現技術創新和體制機制創新,不斷增強維護網絡安全的新思路、新方法、新舉措、新本領,而不是因噎廢食、自甘落后。
二是提出了網絡空間主權。網絡空間主權是國家主權在網絡空間的體現和延伸,網絡空間主權原則是我國維護國家安全和利益、參與網絡空間國際合作所堅持的重要原則。草案雖未作解釋,且一筆帶過,然猶有石破天驚之意。
三是開展國際合作。網絡安全是全球面臨的共同問題,中國對廣泛開展國際合作持積極態度,合作重點包括但不限于網絡治理、技術與標準、打擊違法犯罪等,目標是推動構建和平、安全、開放、合作的網絡空間。
四是建立統籌協調、分工負責的網絡安全管理體制。多年實踐和各國經驗表明,網絡安全工作離不開統籌協調。隨著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的成立,有必要通過立法增強領導小組及其辦公室的權威性。草案規定,國家網信部門負責統籌協調網絡安全工作和相關監督管理工作。具體包括,對監測預警和信息通報、網絡安全應急、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安全防護等跨部門工作,由網信部門統籌協調;對網絡安全審查、重要數據跨境流動安全評估等新出現的綜合性管理工作,由網信部門會同國務院有關部門制定辦法或組織實施。由此,政府向解決分散、多頭和重復管理邁出了關鍵一步。
五是加強行業自律。要充分發揮行業組織作用,指導行業組織成員加強網絡安全防護,促進行業健康發展。
六是強化網絡安全頂層設計。頂層設計至關重要,首先是要制定網絡安全國家戰略,對外宣示主張,對內指導工作;其次要由行業主管部門、其他有關部門制定重點行業、重點領域網絡安全規劃,確保戰略落地,確保這些行業和領域的網絡安全工作有目標、有任務、有舉措、有監督。
七是建立和完善網絡安全標準體系,充分發揮標準在網絡安全建設中的指導性、規范性作用。
八是加大財政投入,以加快產業發展,深化技術研發,提升網絡安全創新能力。
九是做好宣傳教育和人才培養工作。首先,要開展經常性的網絡安全宣傳教育;其次,要通過學歷教育和在職培訓,采取多種方式培養網絡安全人才。
三、關鍵信息基礎設施保護工作進入正軌
關鍵信息基礎設施保護(CIIP)是各國的通行舉措。雖然關鍵基礎設施保護(CIP)涉及物理設施安全,與前者不完全一致,但兩者在多數情況下已可以混用。CIIP/CIP一直是各國網絡安全戰略的重點,有的國家甚至以CIIP/CIP戰略代指國家網絡安全戰略。我們國家在2003年時已經要求“重點保障基礎信息網絡和重要信息系統安全”,并且在實踐中明確了基礎信息網絡是廣電網、電信網、互聯網,重要信息系統是銀行、證券、保險、民航、鐵路、電力、海關、稅務等行業的系統,即俗稱的“2+8”,相關保護工作也常抓不懈。但整體而言,我們與國外差距很大,已是國家安全的軟肋,草案為此設立了“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的運行安全”一節。
一是擴展了保護范圍。縱觀世界各國,凡是已經開展了網絡安全建設的國家,其關鍵基礎設施的范圍幾乎都遠超過我們,例如美國有17類,而我們則有很多重要系統尚未納入保護視野。草案首次明確了關鍵信息基礎設施范圍,包括基礎信息網絡、重點行業信息系統、公共服務領域重要信息系統、軍事網絡、地市級以上國家機關政務網絡、用戶數量眾多的網絡服務商系統。最后一類系統中很多由私企運營,運營者可能對其列為國家關鍵信息基礎設施不適應,但當網絡服務商的用戶達到一定規模時,其安全已經不再是企業自身問題,而成為一個公共問題、社會問題甚至國家安全問題,理應承擔更多責任。一些國外機構可能會拿這個做文章,但事實上美國的關鍵基礎設施有87%受私營企業控制。
二是明確了保護要求。等級保護是1994年《計算機信息系統安全保護條例》提出的制度,其對全國各類信息系統提出了分五個等級的通用安全要求。恰恰因為通用,這個要求只能是基線(即基本要求),其有必要但并不足夠,特別是不足以反映應用模式日趨復雜的異構系統的動態防護需求。此外,保護關鍵信息基礎設施涉及很多工作,不僅僅是提出系統自身的保護要求、加強系統安全建設那么簡單,還包括一系列的管理工作和公共平臺建設,不能由一項制度取代其他制度,理應對此建立專門制度。草案提出,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安全保護辦法由國務院制定。對于某些重點要求,如網絡安全審查、風險評估等,草案則在具體條款中進行了明確。
三是劃定了保護責任。草案規定了關鍵信息基礎設施運營者的安全保護義務,解決了其保護責任模糊不明的問題。他們有必要從國家安全角度承擔防護責任,但這個責任畢竟是有界限的。大家希望知道做到什么程度就無責了,也關心自身的權利如何保障。對很多重點行業的信息技術或網絡安全部門來說,這不僅僅是免責的需要,也是推動工作的需要,因為這些內設機構如果沒有強制性依據,很難得到業務部門的配合。此外,以前我國重點行業的網絡安全監管責任也很不明確。似乎誰都可以進入機房檢查,但誰都不用負責,重點行業往往無所適從、疲于應付。為此,草案明確了行業主管部門的監督指導職責,這是一個重要進步。考慮到關鍵信息基礎設施保護的確涉及多個部門,草案授權國家網信部門統籌協調有關部門,建立協作機制。特別是在網絡安全檢查工作中,要杜絕某個部門前腳走,另一部門后腳來的現象。
四、兼具綜合法與專門法的特點
網絡安全包含的內容太多,當前需要立法規范的事項也很多,于是就有了綜合法與專門法的爭議。一個基本事實是,目前世界上鮮見網絡安全的綜合法,有名的美國《計算機安全法》實際上針對的是美國聯邦政府信息系統安全保護,近幾年美國國會討論的《網絡安全法》或《網絡安全增強法》則主要解決關鍵基礎設施的安全保護問題。
作為第一部網絡安全法(《電子簽名法》不應該計算在內),草案首先要體現綜合性,其側重點應該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要明確部門、企業、社會組織和個人的權利、義務和責任。
二是規定國家網絡安全工作的基本原則和理念。
三是將成熟的政策規定和措施上升為法律,為政府部門的工作提供法律依據,體現依法治國要求。這首先是政府部門的工作需要(如對境外違法信息予以阻斷、實施網絡通信管制等);其次,這些規定和措施往往經過了實踐檢驗,部門間爭議較小,有利于提高立法效率。
四是建立國家網絡安全的一系列基本制度、形成制度框架,這些基本制度帶有全局性、基礎性,是推動基礎性工作、夯實基礎能力所必需。
此外,為了突出實用性,草案還應部分體現專門法的特點。這應從三個方面去考慮:
一是實施重點防護,對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網絡信息內容等重點安全關注予以優先考慮。
二是防范重大威脅。例如,信息系統安全受控于人是我們面臨的心腹大患,斯諾登事件使我們進一步看清風險所在,這就要對供應鏈安全進行規范。
三是對普遍性、長期存在的社會訴求予以響應。
總體看,草案比較好地處理了綜合法與專門法的關系問題,但個別條款還是過于糾結細枝末節(如網絡運營者的分項安全保護義務不必展開),或細致到了足可取代部分專門法的地步(如個人信息保護應制定專門法,原有條款似可刪減后將重心轉向規范信息內容安全)。除了個人信息外,草案沒有突出對公民個人權益的更多保護,如對危害網絡安全行為的舉報并不是為了解決公民作為受害者“報案無門”的困窘,這不能不說是小的遺憾。
五、“網絡安全”的定義還可以更為妥帖
“網絡”和“網絡安全”是“網絡安全法”的題眼。但草案給出的這兩個定義卻使整篇草案黯然失色,效果有云泥之別。近年的工作中,我們用過“信息安全”,也用過“網絡安全”,學者們各抒己見,一些部門也喜歡朝向有利于自身職能的角度去解釋,這些自不待言。但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成立后,已經基本將其統一為“網絡安全”。當然,國安委還是使用“信息安全”,《國家安全法》使用的是“網絡與信息安全”,但這些已不會造成工作上的障礙。
只是這個“網絡安全”實是“Cyber Security”之譯,非“Network Security”。這里面的“網絡”其實指的是“網絡空間”(Cyberspace)。因此,當草案試圖從“網絡空間”的內涵上去解釋“網絡”時,便挑戰了大眾的科技常識底線,且出現了“網絡是指網絡和系統”的尷尬。當然,如果就這么用下去,倒也自成一脈,但草案轉眼就去使用狹義的“網絡”了,如“建設、運營、維護和使用網絡”、“網絡基礎設施”、“網絡數據”、“網絡接入”等,這里都是指的“network”。由此,草案中頻繁出現自己與自己打架的情況。
而草案中的“網絡安全”定義也需修改。現有定義不但丟掉了信息內容安全,更是與“網絡空間主權”沒有關聯。
解決這個問題的途徑是,網絡就是網絡,不要讓網絡去包括信息系統。即,自始至終使用傳統意義上的“Network”概念。對于“網絡安全”,則按“網絡空間安全”去解釋即可。
另外,草案的起草堅持問題導向,對一些確有必要,但尚缺乏實踐經驗的制度安排做出原則性規定。這一處理十分務實、有益,但對于什么是“原則性規定”則要仔細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