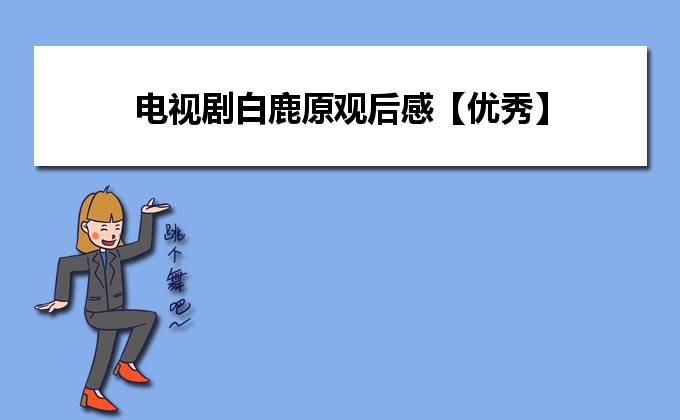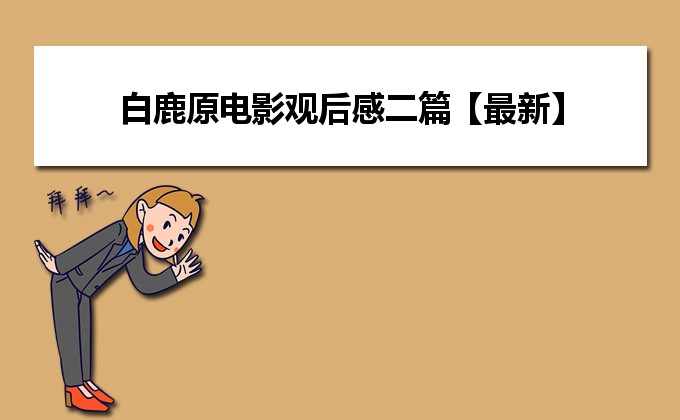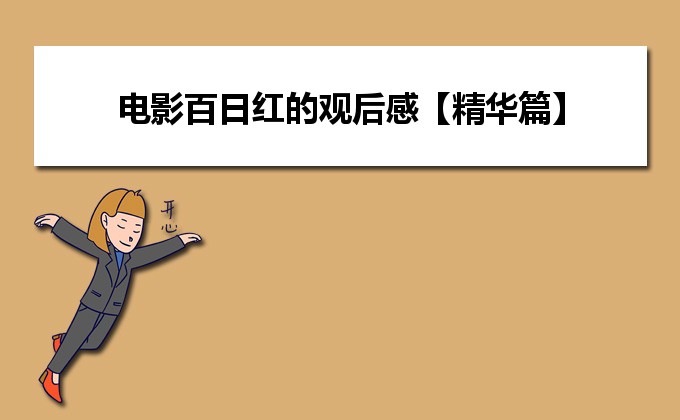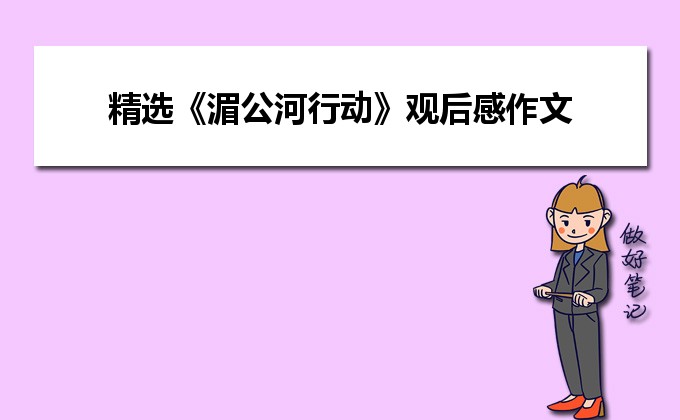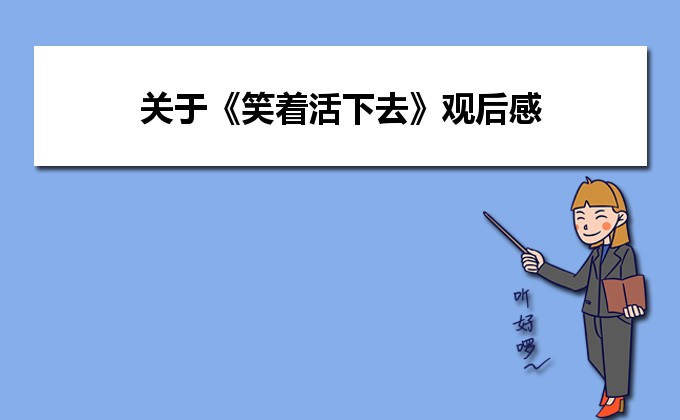感謝觀影club的票,在百麗宮影城國(guó)貿(mào)店的專場(chǎng)觀看了這部作品。
拍攝名著改編的電影一直是很有風(fēng)險(xiǎn)的事情,因?yàn)楹芏嗳硕紝?duì)名著有著先入為主的印象,這種印象是通過(guò)文字語(yǔ)言的勾勒而在腦海里喚起的,它必然是帶著自己的視域想象出來(lái)的,從而有很強(qiáng)的私人性,也就是所謂的一千個(gè)人心中有一千個(gè)哈姆雷特。當(dāng)用視覺(jué)語(yǔ)言重新表現(xiàn)那些文字語(yǔ)言寫成的名著的時(shí)候,就會(huì)產(chǎn)生落差,文字可以描寫一個(gè)人的美麗,但即使極盡鋪陳之能事,它在不同人心中喚起的仍然是不同樣子的美人,而視覺(jué)語(yǔ)言直接把這種美麗固定下來(lái),它摒棄了浮想聯(lián)翩,觀眾所能做到的就是接受導(dǎo)演的視域創(chuàng)生出并拍攝下來(lái)的影像或者厭惡它。比如陳英雄的《挪威的森林》出來(lái)之后,很多人慘叫“這貨不是直子!”
但這部電影并未因此類情況使人產(chǎn)生失望之感,多數(shù)拍磚者不喜歡的僅僅是:它不忠于原著。其實(shí),改編作品并不是一定要忠于原著,拍出自己的風(fēng)格就好。從這個(gè)意義上來(lái)說(shuō),撇開(kāi)《白鹿原》原著,單從電影呈現(xiàn)出來(lái)的故事的角度,這也是我感興趣的那種作品。面對(duì)時(shí)代洪流,老輩人對(duì)傳統(tǒng)的堅(jiān)守與小輩人選擇獨(dú)立道路之間一直會(huì)有沖突,而這批年輕人老了之后仍舊會(huì)遭致下一代的反叛,他們同樣也會(huì)堅(jiān)持自己的傳統(tǒng)恍如他們年輕時(shí)沒(méi)有反叛過(guò)一樣。這甚至就是希臘神話般宿命的現(xiàn)實(shí)。
由于有多種沖突存在,所以可以做很多種解讀,比如族長(zhǎng)白嘉軒與兒子的沖突,雖然并沒(méi)有多少口角,但是影片開(kāi)篇鞭打幼小的兒子,影片中部鞭打那長(zhǎng)大的兒子,都可以做父權(quán)解讀,而兒子的陽(yáng)痿更是中國(guó)現(xiàn)代小說(shuō)的常用橋段了,祠堂的象征意義也很明顯。再比如黑娃因?yàn)楦赣H鹿三殺死了田小娥而削父親的頭發(fā),也可以做弒父的解讀。還有比如族長(zhǎng)與鹿子霖之間的爭(zhēng)斗,可以看作是傳統(tǒng)兩大勢(shì)力的沖突。
但是,由于他們的角色承載了太多的符號(hào),所以人物臉譜化的情況也就多些,造成了角色塑造方面的弱勢(shì)。張豐毅的面無(wú)表情有氣無(wú)力堅(jiān)持到影片結(jié)束都沒(méi)有變化,既沒(méi)有演出來(lái)為父的威嚴(yán),也沒(méi)有演出來(lái)族長(zhǎng)的氣勢(shì)。鹿三全場(chǎng)一個(gè)形象,就是高聲喊叫。黑娃全無(wú)心理變化的交代。事實(shí)上,除了白孝文那符號(hào)化的改變之外,整個(gè)電影都沒(méi)有心理變化的表現(xiàn),即使是導(dǎo)演濃墨重彩刻畫的田小娥。
而之所以塑造角色沒(méi)有立體感,與導(dǎo)演的鏡頭語(yǔ)言有很大的關(guān)系。導(dǎo)演拉遠(yuǎn)鏡頭,著重刻畫全景,常常見(jiàn)到鏡頭內(nèi)滿滿當(dāng)當(dāng)?shù)娜撕孟衲九及愕胤胖迷谝?guī)定區(qū)域,舞臺(tái)風(fēng)格很明顯,這種風(fēng)格在刻畫批斗的時(shí)候是很適合的,當(dāng)被捆綁被批斗的一幫人在下一個(gè)鏡頭氣宇軒昂地成為批斗者的時(shí)候,你方唱罷我登場(chǎng)的滑稽景象讓人噓唏。但是,在其他時(shí)刻,這種鏡頭語(yǔ)言也使人遠(yuǎn)離了人物,看不到人物內(nèi)心的掙扎與沖突,只有外在的形式感的沖突不足以使人物立體起來(lái)。
整個(gè)影片用金黃的麥子作為基調(diào),繼續(xù)秉持了第五代導(dǎo)演喜歡顏色的偏好,但是不斷地用它和牌坊作為轉(zhuǎn)場(chǎng)的方法實(shí)在不高明。鹿子霖與田小娥的那段剪地莫名其妙,應(yīng)該是總局干的。而且黑娃在割麥子的鏡頭貌似與開(kāi)場(chǎng)的割麥子鏡頭重復(fù)使用了?放火燒麥子的第二天沒(méi)有麥子燒焦土地?zé)阽R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