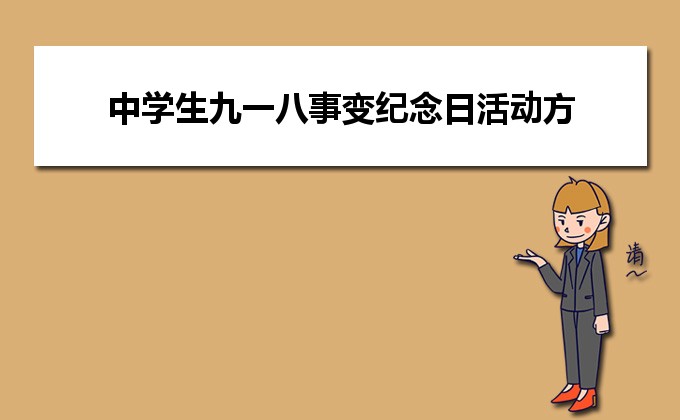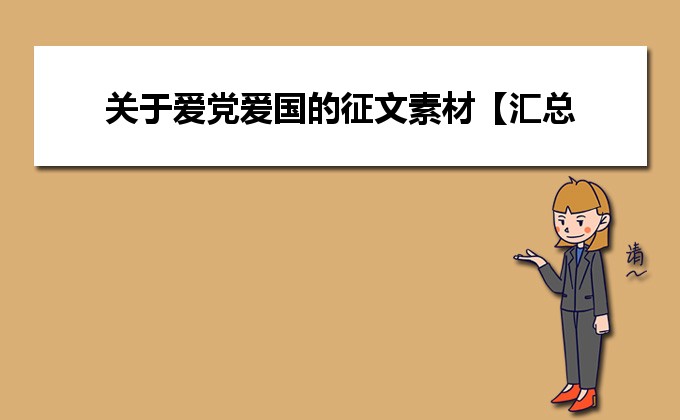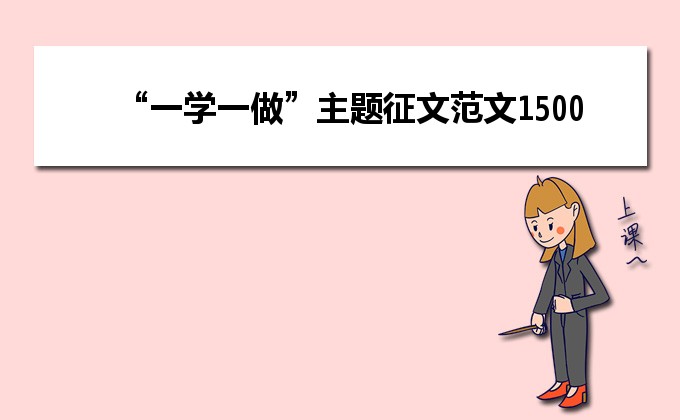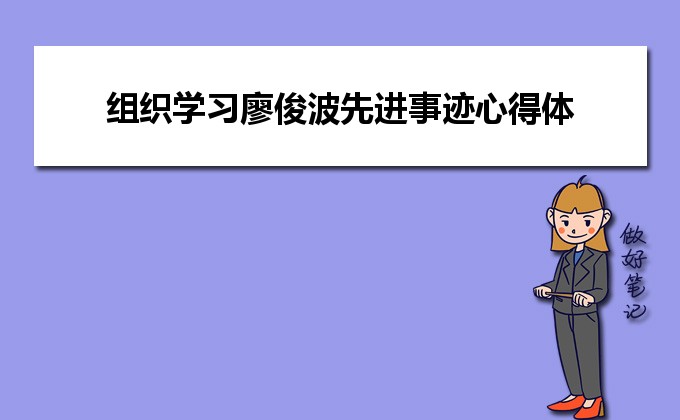你們對于九一八事變了解嗎?如果不是很了解的話,你們可以看看下面小編整理的九一八事變征文材料,供大家參考,希望對你們有幫助。
九一八事變征文材料【一】
九一八事變(又稱奉天事變、柳條湖事件)是日本在中國東北蓄意制造并發動的一場侵華戰爭,是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的開端,也是中華民族進行全面抗戰的開始。1931年9月18日夜,在日本關東軍安排下,鐵道“守備隊”炸毀沈陽柳條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滿鐵路路軌,并栽贓嫁禍于中國軍隊。日軍以此為借口,炮轟沈陽北大營,是為“九一八事變”。次日,日軍侵占沈陽,又陸續侵占了東北三省。1932年2月,東北全境淪陷。此后,日本在中國東北建立了偽滿洲國傀儡政權,開始了對東北人民長達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統治。“九一八事變”是日本帝國主義長期以來推行對華侵略擴張政策的必然的結果,也是企圖把中國變為其獨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重要步驟。它同時標志著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開始,揭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東方戰場的序幕。
九一八事變征文材料【二】
皇姑屯事件關東軍幫倒忙自亂日本政府陣腳
前幾期《重讀抗戰》中我們已經提到,在張作霖多年來引狼入室的賣國之下,日本在東三省獲得了大量的利益,被稱為“滿蒙利益”,日本也將東三省視為“滿蒙生命線”。
1927 年,廣東國民政府的北伐節節勝利,奉軍的敗退和中國統一的趨勢震動了一向把中國的滿蒙視為自己生命線的日本。田中義一組閣不久即出兵山東阻止國民革命軍北進,而且召開東方會議研討對付張作霖和解決滿蒙問題的方法,做出了 “萬一中國戰亂波及滿蒙,有害及日本特殊權益之處時,不問其為中國之任何方面,日本均將對之采取適當措施”和 “對張作霖鐵路土地商租及違約問題繼續交涉”之決定。
田中這么做是因為他認為在南北對抗不利,北伐軍大舉北上的形勢下,只要日本“馴服”有術,已經有點“不聽話”的張作霖仍會“回心轉意”。在他們看來這個合作多年的代理人仍有相當的利用價值,仍然是華盛頓體系下日本攫取在華利益的最佳代理人選。
因此田中希望在蔣介石統一中國本土之前,有必要使張作霖先同意商租權和敷設滿蒙五鐵路的問題。如果用條約的形式保證了這些權利,那么,即使革命波及滿蒙,田中自信日本能使那時候的當局無論是張還是蔣承認這些條約。
為防止或延緩革命軍的北進,日本外務省采取公開支持張作霖的路線,“讓張迅速返滿,以便維持東三省治安”,在此情況下,山本條太郎來到北京強迫張簽署五鐵路合同,張因日本有掩護他撤回關外且幫助阻止北伐軍出關的許諾,5月7日同意秘密簽署,5月13日簽了延海、洮索兩線合同,5月15日簽了吉敦延長線、長大線合同,這4條鐵路定于3個月后開工,吉五線則留待去奉天簽。正是這個留有尾巴且沒有換文的密約成為后來日本向張學良多次要求交涉的依據。關于《滿蒙新五路協約》的簽訂,山本條太郎曾得意地說:“這等于購得了滿洲,所以不必用武力來解決了。”
與田中內閣的打算不同,日本關東軍的打算是除掉張作霖,在東北制造動亂,于亂中建立親日政權。6月4日張作霖從北京乘專列撤至皇姑屯時被關東軍過激分子秘密炸死,是為皇姑屯事件。該事件發生后,東北局勢并未朝著肇事者關東軍所希望的亂中取勝的方向發展,反倒是打亂了田中的外交部署。特別是《滿蒙新五路協約》的簽字文本在皇姑屯的炸車中隨張作霖的列車灰飛煙滅,令田中長時間來的努力頓時化為泡影。之后日本所有試圖讓張學良承認此條約的努力都相當于從0開始。
以田中為首的逼張派根本沒有料到關東軍真會干掉張作霖。據田中義一的長子田中龍夫(原眾議院議員)說:田中首相接到這一情報時,正在吃飯,不由得摔掉筷子冒出一句:“糟了!”,他非常憤怒地說:“陸軍干出這種事來,使我們的計劃化為泡影”。??豬一樣的隊友完全幫了倒忙,田中原本絲絲入扣的計劃頓時陣腳自亂。
東北易幟日本更加被動
而更加讓田中內閣被動的是“東北易幟”。
日本對于“東北易幟”南方國民政府的態度,在1928年7月16日林久治郎特使拜訪張學良的時候已經徹底揭露:林十分清晰地表達了這一立場,他說:“(南京)國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同我國在東三省保衛既得權益方針是絕對不能兩立的,與南方合作就無異于同我國對抗。”
對于張學良易幟的謀劃,日本方面的對策主旨是“堅決阻止東三省政府同南方合作”,并軟硬兼施。一是向張學良強硬表示,“如果同南方妥協,將嚴重傷害兩國關系”;一是采取收買策略,“假如張學良不傾向南方,恪守保境安民的中立態度的話,日本愿支持張學良的現在地位,并考慮協助抵抗南軍的進攻”。
日本在東北易幟時間上的強硬(也是對中國內政的干涉)引起了英、美各國的不滿,他們以日本干涉中國內政違反華盛頓條約,向日本政府一再施加壓力,日本在野黨也乘勢指責田中內閣的對華政策,加強了反對田中內閣的活動,田中內閣開始陷于內外交困的境地,在國際輿論的壓力和日本國內形勢的演變下,1928 年 11 月,田中不得不暫時有所收斂了對中國東北易幟的干涉,在日皇加冕典禮上,特向張學良派去的特使莫德惠等人承認東北易幟是中國的內政問題,表示: “東北易幟事,只要維持日本在滿蒙的既得利益即不反對。”這一表態標志著,原本試圖繼續進一步竊取中國東三省利益的日本政府,在關東軍皇姑屯事件幫倒忙自亂陣腳的干擾和東北易幟事件的進逼下,已經被迫追求維護已得利益的防御態勢。
而很快,在田中內閣倒臺后,濱口雄幸組建的內閣中,整個20年代主持日本外交提倡融入華盛頓體系,對中國不干涉內政的幣原喜重郎再次擔任外相,新內閣宣布:“刷新日中邦交,敦睦善鄰之誼為當前一大急務”。東北的外交態勢進入最有利的環境中。
九一八事變征文材料【三】
張學良所在的位置本可承擔外交緩沖作用
在張學良面前的,是一個微妙的外交格局。一方面6月9日,國民革命軍進入北京,完成了北伐。在濟南事件后的日益高漲的反日民族運動推動下,7月7日國民政府宣布廢除不平等條約,中國掀起了收復國權運動的潮流。
另一方面,日本方面的表態言猶在耳“(南京)國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同我國在東三省保衛既得權益方針是絕對不能兩立的,與南方合作就無異于同我國對抗。”、“東北易幟事,只要維持日本在滿蒙的既得利益即不反對。”
兩者之間是絕對的對立:日本追求的是保護已有的“滿蒙利益”,而南京國民政府的“革命外交”、“廢約”、“收復國權”則不能容忍日本的“滿蒙利益”。
兩者之間的絕對對立,同時也提供了極大的外交縱橫捭闔的空間。東北易幟后的張學良集團,正好擁有得天獨厚的條件:服從南京國民政府,但在財政、外交、軍事、交通等各方面又保有相當的獨立性,正可在日、蔣間予以外交彌縫填補,以保證東北領土主權的安全:一方面擺出與日本可以合作的態度,使日不會因“滿蒙利益”斷然無望而鋌而走險,破壞華盛頓合約對東北進行直接軍事占領??就是后來九一八事變發生的那樣;另一方面則可利用外交態勢的改善,經由談判漸次回收被張作霖大賣特賣的權益。同時也給予幣原在“滿蒙利益”上實際交涉的“外交成果”,從而使其可以壓制日本國內的激進派力量。
如此操作,需要操作者本身具有長遠的政治眼光和真正的政治智慧,以及圓滑、靈活的外交手腕。
而張學良恰好不具備。
張學良的無能導致無法勝任
張學良曾說:“我父親是想和日本合作的,我自己也是同一心情。但干這種事的正是日本人,我怎么還能與日本合作呢?換句話說,我父親與日本人合作被殺了,如果我還和日本合作的話,那不是我比我父親更容易被暗殺嗎?因此我不能和日本合作,合作就是賣國賊”。
這段話實際上承認了其父張作霖的賣國賊身份。但另一方面也說明的是,他真正是因為“不是我比我父親更容易被暗殺”而“不敢”。
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他沒有這個才能。
對于接任其父的職務,張學良一直以自己資歷不夠推讓不就,他剖析自己不堪重任時說:
“我的性情:放逸、急躁、嫉惡如仇、不能容忍。徒有求治之心志,而乏治理之才能,不適于軍政大任。”
這話非推脫之語,而是實情。
張學良面對的政治變局比張作霖時代更加變幻莫測。而其需要面對的對手,無論是已經在東北獲得巨大利益的日本,還是北伐氣勢正盛的國民政府,都比張作霖一直要面對的對手更加強大和難纏。張作霖的死已經證明,他那種小聰明加流氓式的外交手腕已經無法應對,更何況連小聰明都沒有張學良?
而張學良麾下,又繼承的是瀕臨絕境、僅靠一點封建意識和死者余威勉強維持的政治集團。
張學良由此從心底發出慨嘆:“我沒有我父親的能耐……我應付不了。”
沒能耐、應付不了??這是張學良的真心話。
于是,張學良的選擇,讓最好的外交態勢得到了最差的結果。
因為自覺應付不來,張學良面對日本方面的外交交涉,干脆直接踢給國民政府處理。本來外交方面,總的說權力歸于中央政府,但東北亦有自行外交活動。張學良與蔣介石商定,東北外交完全歸中央辦理,而在內部決征詢張學良之意見。此后南京政府控制了東北的外交機構并直接任命東北外交官員。到九一八事變前夜的萬寶山事件時,南京政府外交部稱,萬寶山事件是地方事件,由地方當局處理,但當時負責對日交涉的是外交部駐吉林特派員鐘毓,對日交涉是在南京政府的主導下進行的。
又如面對日本對《滿蒙新五路協約》的交涉,張學良聲稱鐵路交涉問題須由中央政府作主,而南京國民政府早在 1927 年 11 月 23 日二次北伐前發表的四項聲明里第三條 “未經國民政府參與而進行修改和批準的條約一律無效”; 第四條 “有關中國的條約而國民政府未曾參與者,對中國無約束力”。此后,但設此類交涉張學良就以“需要國民政府的同意”之語回避日方提出的要求。張學良自己固然不再有責任,但原本可以在日、蔣間起到的外交緩沖作用也就完全不存在了。
張學良的不愿和不能作為,讓態勢回到了日蔣直接對立的狀態:日本視為必須守住的既得“滿蒙利益”蔣政權視為必須不能存在,雙方連談判的空間也不存在。連一直以來對華使用不干涉內政協調外交的幣原,也對此束手無策。
幣原決定先解決現實問題,同中國締結關稅協定,對棘手的“滿蒙懸案”日后待機提出再議。1930年1月11日,日本代理公使重光葵與中國外長王正廷簽訂《中日關稅協定》,南京接受在3年內不增加主要日貨關稅,并允償還“西原借款”等舊債。日本承認中國關稅自主權。重光葵在其著作評論道:這是“幣原外交”的“全盛時期”。1930年,“日本政府和軍部都同國民政府建立了良好關系”。兩國邦交“開始走上了正軌。”
但事實上,“良好關系”只是假象,雙方在最核心的“滿蒙利益”上沒有談判空間,原因在于,本來可以存在的緩沖空間,被張學良的“應付不來”和“不能”直接壓縮為零,幣原也只有一招“拖”而不決。
也因此,向以“協調外交”為標榜的幣原外交,屢屢被國內激進勢力抨擊為 “軟弱外交”、 “迎合外交”。1931年1月24日,滿鐵總裁松岡洋右在日本國會上公然提出:“滿蒙問題關系到我國的存亡問題,是我國民的生命線,無論在國防上、經濟上均是如此”,接著,松岡質疑 (濱口)內閣 “成立一年半以來,究竟在滿蒙之地有何作為?”指責幣原外相 “絕對無為的旁觀主義”。幣原喜重郎答辯稱, “對松岡君的批評感到意外”,并闡述他的 “外交經濟化”。但幣原的辯駁毫無疑問是無力的,日蔣雙方在“滿蒙利益”問題上勢同水火已經人盡皆知,并在日本國內引起了巨大的要求“強硬”的民間呼聲。
關東軍倒是在1929年就已經明白地認識到張學良不愿也無能作為的最終結果。1929年5月1日,在旅順召開的關東軍“情報會議”作出結論:張作霖死后,日本解決滿洲問題,除行使武力之外,別無選擇。
九一八事變不發生,東北不淪陷的可能,就這樣被張學良揮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