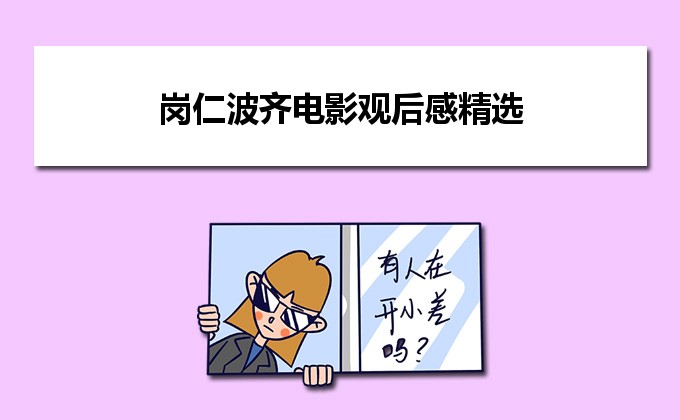篇一:關(guān)于信仰的影片《岡仁波齊》觀后感
岡仁波齊。看到后面三個(gè)字,你大概能想到“仁波切”,不要懷疑,這就是同一個(gè)詞,藏語里表示“珍寶”,岡是“雪”的意思,所以用漢語翻譯,岡仁波齊叫做“珍雪神山”也未為不可。
從地圖上看,岡仁波齊在西藏的西側(cè),芒康在東側(cè),中間差著2000多公里,大部分路程在318國道上,途經(jīng)藏地小江南林芝和圣城拉薩,“隔山不同天,一天有四季”,景色美翻,騎行者的最愛。
如果說當(dāng)代有什么具有代表性的文學(xué)意象,“在路上”算一個(gè)。
《岡仁波齊》是一群藏族人“在路上”的故事。
不同于都市氣息濃烈的打打鬧鬧迷茫困惑的“路上”,這里的“路上”安靜無比,路上只需要做一件事:磕長(zhǎng)頭。
巧的是,樸樹為前者吟唱了《平凡之路》,又為后者唱了《no fear in my heart》。在前者中,他發(fā)現(xiàn)了平凡是唯一答案,后者中,他發(fā)現(xiàn)只有放手墜落,那個(gè)“真正的我”才會(huì)誕生。
始終在迷失和尋找,沒完沒了。人生就是這么個(gè)過程。
2015年是藏歷羊年,梅里雪山的本命年。當(dāng)時(shí)我在青海囊謙縣,我身邊的藏族朋友幾乎都竭盡所能去梅里雪山的主峰卡瓦格博轉(zhuǎn)山。他們有一種魄力,說走就走,全家一起走。那天我給村支書打電話問點(diǎn)事兒,他說自己正在舉家開車前往云南轉(zhuǎn)山,過一陣再回來。
后來我聽說村長(zhǎng)也去了,轉(zhuǎn)完山,順便上大理麗江逛一圈,花費(fèi)一個(gè)月左右。
我覺得對(duì)于平凡的人們來說,這算是一種旅游休閑方式。他們信馬由韁的狀態(tài),比我要瀟灑得多。
岡仁波齊的本命年應(yīng)該在梅里雪山之前,2014藏歷馬年。在神山的本命年前往轉(zhuǎn)山,功德殊勝,這是很強(qiáng)大的動(dòng)力。影片中的幾位村民,有各自的不如意和期望,他們要通過這次朝圣來完成各自的小目標(biāo)。于是帶上帳篷和干糧就出發(fā)了。
“嘩”,手板在公路上擦出聲響,周而復(fù)始的磕長(zhǎng)頭開始了。
馬達(dá)聲、喘氣聲、說話聲、風(fēng)吹來的聲、雪落地的聲、柴燃燒的聲……
配樂?對(duì)不起,《岡仁波齊》沒有。
在靜默之力中,一切精心打磨過的旋律或許都是噪音。
影院里,總是缺少一種讓人靜下來的東西,這部影片有。
不吹不黑,不夸張,也不一驚一乍,平靜地表現(xiàn)一群人的朝圣之路。藏族人的生活觀、生死觀在這條路上生動(dòng)展現(xiàn)。
有評(píng)價(jià)說朝圣路上的人,不卑不亢、無喜無悲。這八個(gè)字對(duì)了一半,不卑不亢是一種態(tài)度,無喜無悲哪來的人生呢?
朝圣者并不在乎外界的評(píng)價(jià)嗎?未必。
磕長(zhǎng)頭很難,不是每個(gè)人都能做到,做到的人,會(huì)受到普遍的尊敬。
但在拉薩配合拍攝時(shí),片中的主角也曾被其他人吐口水,一如網(wǎng)上的指責(zé)聲。
我們都在用自以為正確的方式去解決人生的問題。難的,是如磐石般堅(jiān)信。
誠如導(dǎo)演所說,這個(gè)世界上沒有什么生活方式是完全正確的,但若干年后,人們?nèi)钥梢詮倪@部影片里,看到有一個(gè)民族還這樣生活過。 神山圣湖不是終點(diǎn),接受平凡的自我,但不放棄平凡的理想和信仰,熱愛生活,我們都在路上。
既然都在路上,那么你早已出發(fā),只是沒意識(shí)到罷了。
我很喜歡影片中的一個(gè)設(shè)定:剛降生的嬰兒與大人們?cè)诔ヂ飞下L(zhǎng)大。其寓意簡(jiǎn)單而深刻:即使你無所事事地過完一整天,你也在路上。即使你的目的地不是岡仁波齊,你也在路上。
從出生開始,你就在一條通往死亡的路上。真正把人區(qū)別開來的,是你在路上做什么。
我們?nèi)绱松瞄L(zhǎng)自省,同時(shí)也擅長(zhǎng)美化他者。擅長(zhǎng)將希望寄托于遠(yuǎn)方,將躁郁流放于憧憬。
而總是忽略了:不動(dòng),也是修行。
最后請(qǐng)?jiān)试S我掃掃興,說一件小事。轉(zhuǎn)山或許是為了清除心中無形的垃圾,但稍不注意,有形的垃圾就會(huì)污染有形的世界。
還是2015年,位于云南省迪慶藏族自治州德欽縣的卡瓦格博,迎來了絡(luò)繹不絕的朝圣者,也由此產(chǎn)生了大量的生活垃圾,垃圾所在的地域山高谷深,運(yùn)力難及,致使垃圾存量龐大,而且不斷增加。在一次為期12天的清潔行動(dòng)后,共清理殘留垃圾150噸。
在環(huán)保意識(shí)上,我想,任何熱愛生活的人,都不難達(dá)成共識(shí)吧。
篇二:關(guān)于信仰的影片《岡仁波齊》觀后感
影視專業(yè)的學(xué)生有一部必看影片叫《北方的納努克》,電影講述的是在北極生活的愛斯基摩人的日常。導(dǎo)演弗拉哈迪是個(gè)采礦工程師,他用隨身攜帶的攝像機(jī)把愛斯基摩人的生活拍下來,剪輯成一個(gè)小短片,拿到紐約放映,按照現(xiàn)在流行的話語方式說『口碑爆棚』。但他吃了沒有硬盤的虧,有次抽煙時(shí)不小心把火星濺到了膠片,引起了一場(chǎng)火災(zāi),素材沒了。
弗拉哈迪不甘心,準(zhǔn)備充分后重回北極,找到了一家愛斯基摩人,在影片中他們被稱作『納努克』,然后跟隨式拍攝。為了配合表演,納努克們忽略了正常的過冬儲(chǔ)備,沒有攢下足夠多的食物,在弗拉哈迪走后的那個(gè)冬天全家餓死了。
《北方的納努克》很好看,憑借人類的獵奇心和冒險(xiǎn)精神,1921年的愛斯基摩人如何吃住過活的情形,通過影像得以保存。同時(shí)期的中國,民國迎來第九個(gè)年頭,電影《閻瑞生》同年上映,成為了中國第一部長(zhǎng)故事片。巧的是,九十多年之后,導(dǎo)演姜文將之改編為《一步之遙》,成了他的又一次滑鐵盧。
姜文也時(shí)常在談到影片時(shí)流露出一些不甘心,但如今不會(huì)再有人說起《一步之遙》,那像是一個(gè)遙遠(yuǎn)的鬧劇了。
說這些是我早上去看《岡仁波齊》時(shí)想到的,電影自誕生起就有紀(jì)實(shí)和幻想之分,會(huì)玩的美國人,把地球摸了個(gè)遍,留下來一個(gè)個(gè)傳奇,小孩喜歡,大人也不討厭,像是看到童年一般坐在孩子邊上看完。
《北方的納努克》就是好電影,有紀(jì)實(shí),也有故事,還有奇觀。如果只是生活,我們直接去看就好,不用拍,在火車站、醫(yī)院待一天就夠編劇寫三年了。好電影是看的時(shí)候如臨其境,看完之后久久回味,它教會(huì)了觀眾一些東西,觀眾也在觀看時(shí)縫合了一些記憶。在影片中,『納努克』們搭建雪屋、捕獲海象、獵殺北極熊、生食海豹??『哦,他們是這樣生活的』??這是我當(dāng)時(shí)的反應(yīng)。
后來一路看下來,電影的光暈越來越單薄了,我也越來越喜歡看老電影。弗拉哈迪是個(gè)優(yōu)秀的故事捕手,他只是把故事搬運(yùn)到當(dāng)時(shí)的大城市紐約給人們看,他知道自己的攝像機(jī)應(yīng)該架在哪里;張揚(yáng)導(dǎo)演則顯得沉浸在故事里了,導(dǎo)致視角是含糊的,有些時(shí)候你分不清楚,這些朝圣的人,他們是本來就這樣,還是被安排成這樣??后者是導(dǎo)致這部影片被批評(píng)的一個(gè)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