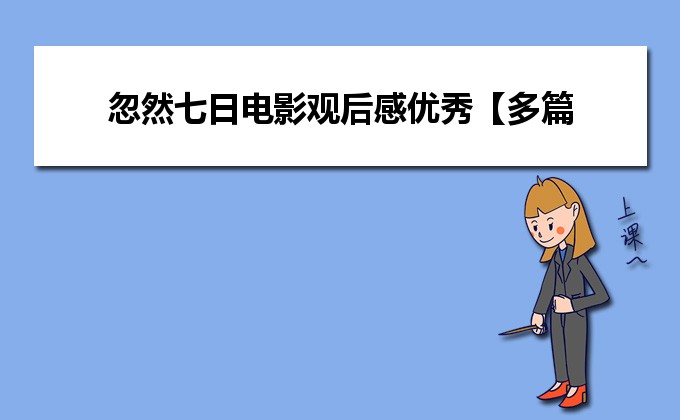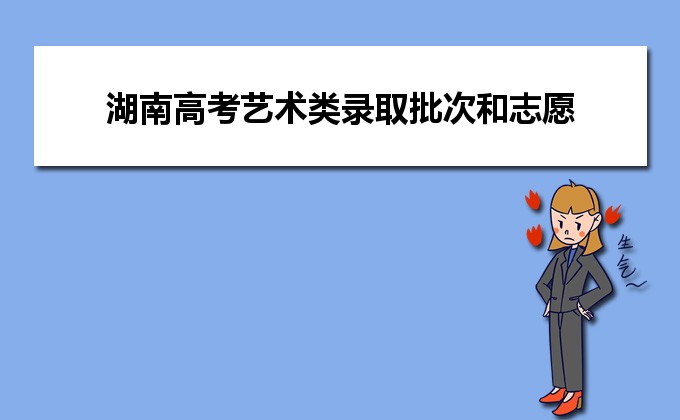武訓一生勞苦,對自己又十分節儉,終因積勞成疾,于光緒22年(1896年)4月23日,在臨清御史巷義塾內(現臨清武訓實驗小學)含笑去世,終年59歲,葬于堂邑崇賢義塾東側。
武訓傳電影觀后感【篇一】
毛批《武訓傳》的社論,其首要的觀點,認為武訓“狂熱的宣傳封建文化,并為了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宣傳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婢膝的能事”,從電影的文本來看,其實根本是站不住腳的。武訓不要牌坊、不要黃馬褂,在受賞的時候裝瘋賣傻,哪里是為了自己的名利和奴顏婢膝呢?在片中武訓從來沒有用過一句四書五經上的話,聽到孩子解釋“學而優則仕”就立刻怔住了,這哪里是“狂熱宣傳封建文化”呢?“革命的農民斗爭的失敗作為反襯來歌頌”,笑話,片子里哪里有“革命的農民斗爭”呢?只有周大的“官逼民反”罷了。
整部片子最要緊的問題,其實是“我們有沒有另一種變革的可能?”在電影中其實已經說得很清楚了。雖然它沒有答案,但是明確指出了方向。武訓出于民、歸于民,他并不要變成民眾的領導者,而只是要做一條供人人走的路,一條體民之心又助民成事、聚民之財又歸于民用的路。并沒有什么人民的公意在他那里變成政治權力,有的只是懂得道理、不受欺負的一點心愿和老百姓的一個個錢,在他那里變成窮孩子都能夠上的學。而這學的目標,當然不是要回到主子-奴才的腐朽結構中去做一個官,或謀得一個能夠欺壓別人的狗的地位,而是“不忘莊稼人”的學,要使天下的老百姓都有更好的生活。孫瑜借武訓要立的義學,本質上是一種旨在新民的新學,無論是中學西學、古學今學,只要是實實在在的善民、利民之學,我想都是他會支持的好的學問。而有了這新學的新民,方可有真正的新政,人們才不會再墮回腐朽的舊結構之中,或在殺人放火中去體會“為善之樂”。
以毛的敏銳眼光,這些東西他不會看不出,這部電影的“毒性”他不會不清楚。只是他心里想的恐怕是:“我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的道路”。武訓的道路和他的道路的差別,比一比武訓和《姊姊妹妹站起來》中的指導員就知道了。所以,最重要的是黨員同志們應當高舉歷史唯物論的武器??當然這武器是抽象的思想和觀念??來為武訓扣上前面的那幾頂帽子,批判電影中的“具體的歷史事件、具體的歷史人物(象武訓)、具體的反歷史的思想”。當然,最重要的是要批判心中那些具體的感動,用抽象的觀念來純潔我們的心靈,克服“資產階級反動思想的侵入”。
武訓傳電影觀后感【篇二】
1951年5月在全國范圍內展開的,持續半年之久的批判《武訓傳》運動,是新中國思想文化界第一個重大事件。關于開展這場運動的歷史背景以及運動所具的現實意義,在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報》社論《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中已有深刻揭示。
如果我們脫離建國初期的歷史背景、脫離建國初期的政治思想狀況、簡單地機械地從感情出發,去認識和評價這場運動,或者通過否定當初發動批判的“片言只語”,進而采取全盤否定的態度,這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至少很不公平。
況且,1951年6月,毛澤東在審閱一篇稿子時有針對性地加寫道:“我們說,武訓自己怎樣想是一件事,武訓的后人替他宣傳又是一件事。” 明確表示:武訓本人是不重要的,他已經死了幾十年了,武訓辦的義學也不重要,它已經幾經變遷,現在成了人民的學校。重要的是我們共產黨人怎么看待這件事──對武訓的改良主義道路,是應該歌頌?還是應該反對?
一、《武訓傳》首映后社會各界的反應
電影《武訓傳》是在1948年7月由中國電影制片廠正式投拍的。解放后,于1950年2月經過劇本修改后再次投入拍攝。1950年底完成制作。
1951年2月21日晚7時,周恩來、朱德、胡喬木、茅盾、袁牧之等百余位中央領導在中南海某大廳觀看了此片,“大廳里反應良好,映完獲得不少的掌聲。”
江青與毛澤東當晚沒有去看,是在幾天后調看的。據江青說:“看《武訓傳》我們倆人都不高興,主席沒有說話。我說這是改良主義的戲,主席不吭聲。”
社會各界的反應如何呢?1951年新年前后,京、津、滬三大城市的一些報刊,短短的二三個月內連續發表了40多篇肯定和贊揚的武訓和《武訓傳》的文章,出版了一批有關武訓的書籍。這些文章和書籍,對武訓、“武訓精神”和《武訓傳》做了“極為夸張”的歌頌。主要表現如下:
(一)把武訓、“武訓精神”和“革命者”、“革命精神”視為一體。這些文章把武訓描繪成符合新意識形態的要求的“先驅人物”,看作是“中國革命‘譜系’”里的重要人物,甚至于認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都是“師承他們的結果”。
(二)把影片《武訓傳》的意義與當時的“革命運動”聯系在一起:認為影片“在解放后的新中國,應當廣為宣傳,因為這故事有非常大的教育意義。”可以“迎接文化建設的高潮”。
(三)把武訓稱頌為“新民主主義教育的旗幟”。視為“中國歷史上,偉大的勞動人民,企圖本階級從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幟。”“新民主主義的教育工作者應當以武訓為旗幟”,“要按照陶行知教育思想辦教育”,將陶的貢獻與毛澤東相提并論,認為“新民主主義教育思想是毛主席和陶行知共同創造起來的”。
二、難道“解放了的中國人民是武訓事業的繼承者”?
建國伊始,我們雖然國家奉行的是“新民主主義的建國大綱”,但這決不意味著我們忘記了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所規定的共產黨人的“消滅資產階級的歷史使命”和“建設的歷史目標”;同時,新生政權當時從舊社會接收了大約200萬的各類知識分子,他們的政治思想狀況參差不一表現復雜。他們長期生活和工作在舊社會,其中大多數人又出身于非勞動人民家庭,基本上接受的是資產階級教育,就世界觀和立場而言,絕大多數知識分子依然是資產階級的。因其“親美、崇美”的本質,很容易走向共產黨的反面。
有鑒如此,建國初,我們在與資產階級搞“統一戰線”,堅持“團結、利用”他們的同時,也大力對其進行“限制、改造”。掃除“舊政權的社會基礎”和“改造資產階級思想”在當時是一項相對緊迫的任務,目的就是為了盡快的掃除那些“國內外的敵人”賴以存在的社會基礎。
毛澤東對農民的基本理論觀點和態度是:肯定農民的革命立場,珍視農民的革命熱情,倚重農民的革命力量。
對革命的基本主張是采取“暴力革命”、“階級斗爭”、“槍桿子里面出政權”。
他認為:所有寄希望于既有統治階級的改良主義都是錯誤的、反動的。
如果按照上述觀點來觀察這部電影,毫無疑問,《武訓傳》所宣揚的“讀書救窮人”,“階級合作”,“武訓向統治者乞求、下跪”等內容,恰恰和農民為主體的革命性質背道而馳,是一種階級妥協或者說是階級投降,表現的“改良主義”實質上就是“投降主義”。
三、首先扯起批判《武訓傳》大旗的是江青
前面說過,當初毛澤東和江青看了《武訓傳》后,毛澤東沒有表態。江青說“這是改良主義的戲”,毛澤東“沒吭聲”。由于江青對這部電影所設涉及的政治問題相當敏感,所以江青并沒有“善罷甘休”。
她要求主管文藝的文化部負責人周揚,批判這部“宣揚改良主義”的影片。但她的努力很不順利,“沒有一個聽她的”。要求周揚等人批判碰壁后,江青開始專注有關《武訓傳》的評論文章。她是這樣敘說的:“我們黨的高級*也有贊成《武訓傳》的。我帶了材料到主席那里了去,見了一面以后,他就看不見我了。有天突然到我房里來,我滿屋子都是材料。主席說,我到處找你不到,你原來在搞這個。陳伯達、胡喬木路過我們那里,主席告訴他們《武訓傳》的事應引起注意。他們回到北京后,周揚大概覺得不好過了。”
四,毛澤東指示批判要采取“慎重”態度
據林默涵回憶:“電影《武訓傳》出來以后,不少人說好,據說毛主席看了這個片子,幾個晚上在院子里轉來轉去,最后下決心要批判的。”江青收集和送的材料,正好契合了當時毛澤東對各類知識份子的政治作用和思想狀況警惕之心,契合了當時毛澤東對意識形態領域“破舊立新”工作的高度重視之心理。
因為在毛澤東看來,這些連篇累牘的頌揚武訓以及“武訓精神”文章,與電影《武訓傳》一樣,實質上都是表現出“否認階級斗爭,不要政治斗爭,不要武裝斗爭,不去觸發當時人民遭受苦難的基本問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的”,正是資產階級反動思想,使得人們在觀察武訓這個角色的時候,陷入了如此嚴重的錯誤。而這些“錯誤思想”在當時不僅沒有得到阻止、批判,反而受到普遍好評,并且愈演愈烈,很快就“好評如潮”,甚至于許多“學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員”也看不出問題,也去稱贊的武訓的精神,毛澤東認為這是“資產階級反動思想侵入了戰斗的共產黨內”了,由此,毛澤東發出了“我國文化界的思想混亂達到了何等的程度!”的感嘆!
《人民日報》總編輯鄧拓在一次談話中說:毛主席認為,武訓最初是窮人,辦義學的動機也是好的;但是,后來他有了錢、有了地,就脫離了勞動人民。毛主席說,武訓辦學搞的是階級調和、改良主義,而歷史唯物主義認為,只有人民起來搞暴力革命,才能推翻剝削階級的反動統治,才能真正有翻身學文化的機會,中國人民也正是在中國共產黨的勞動下進行武裝斗爭、暴力革命才取得了勝利,而不是靠甚么辦義學,走教育救國、知識救國等改良主義的路。而在現在這個時候用文藝作品歌頌武訓就更不應該。
顯然,組織對《武訓傳》的批判是為了求得澄清中國思想文化界的“混亂思想”,而不是為了追究“個人責任”;由于當時奉行“建立新民主主義”政治路線,所以,毛澤東在強調要進行嚴肅批判的同時,又要求批判運動中執行“對事不對人”政策,即對人的處理上是采取比較慎重的態度。
五、軟弱無力的批判沒有達到意義特殊的政治效果
毛澤東提出批判意見后,周恩來很快執行毛澤東的意見。并且在貫徹過程中,連帶做了一些自我檢討,為《武訓傳》承擔責任。根據《周恩來年譜》記載:1951年3月24日,召集沈雁冰、陸定一、胡喬木等開會,研究加強對電影改造領導的問題。
文藝界的主管周揚得知批判《武訓傳》是毛澤東的意見后,他在當年3月召開的全國文化行政會議上,批評了《武訓傳》,并開始檢討。
胡喬木當時主管著宣傳、新聞、輿論工作,直接出面組織文章。
綜合各方面的批判動態,包括大多數批判文章,都認為武訓的錯誤是“對統治階級的軟弱”和“不去斗爭”的改良主義,但也都強調,武訓的“動機然是好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只是“在當時的政治條件下,是不可能實現他的愿望的。”
文章的用語都十分委婉,不潑辣,不尖銳,針對性和戰斗性不強。所以,這些文章最大的特點正如5月20日《人民日報》社論所說的“雖然批評武訓的一個方面,仍然歌頌其他方面”。這些“吞吞吐吐、含含糊糊”文章,不僅沒有徹底否定武訓,反而在討論中被反覆質疑、反詰而顯得理屈詞窮。
一個多月的批判證明,這種相對溫和的批判達不到特定的政治效果。批判運動要實現特定的政治目的,靠正常程式,以黨內通知的方式是不夠的,必須采用“非常方式”,以更大規模,更為激烈的方式進行才能奏效。
六、必須旗幟鮮明制止文化界的思想混亂
眼見批判的軟弱無力,人們對“武訓精神”崇拜依舊, 1951年4月底,毛澤東決定親自指揮一場“意識形態領域的大斗爭”。既然這種“鈍刀子割肉”式的、小規模的、溫和的批判已經證明是達不到意義特殊的政治效果的,為此,必須造成特殊的政治效果,并盡可能地發動更多人參與,以更大規模地教育人們、改造思想。
毛澤東指示胡喬木為《人民日報》寫一篇社論。然而,胡喬木寫的社論稿子遲遲出不來,出來的稿子仍沒有達到毛澤東的要求。毛澤東于是親自把胡喬木的稿子幾乎全部改寫,只是特意留下了“一個不完全的目錄”,即保留了京、津、滬三城市的“報紙和刊物上所登載的歌頌《武訓傳》、歌頌武訓、或者雖然批評武訓的一個方面,仍然歌頌其他方面的論文的一個不完全目錄”。
5月20日,《人民日報》第一版醒目地推出社論:《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這是《人民日報》第一次為批判一部電影而發表社論。更重要的是,這篇社論主體由毛澤東親自撰寫。文章簡單明快的點出“《武訓傳》所提出的問題帶有根本的性質”,并且尖銳地說明了開展批判《武訓傳》的原因。與社論相配合,同日,《人民日報》“黨的生活”專欄,用毋庸置辯的口氣,發表了號召批判電影《武訓傳》的要求。
“……像武訓那樣的人,處在清朝末年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者和反對國內的反動封建統治者的偉大斗爭的時代,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并為了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宣傳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婢膝的能事,這種丑惡的行為,難道是我們所應當歌頌的嗎?《武訓傳》向著人民群眾歌頌這種丑惡的行為,甚至打出“為人民服務”的革命旗號來歌頌,甚至用革命的農民斗爭的失敗作為反襯來歌頌。這難道是我們所能夠容忍的嗎?”
“《武訓傳》所提出的問題帶有根本的性質。……電影《武訓傳》的出現,特別是對于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歌頌竟至如此之多,說明了我國文化界的思想混亂達到了何等的程度!……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號稱學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員。他們學得了社會發展史──歷史唯物論,但是一遇到具體的歷史事件,具體的歷史人物,具體的反歷史的思想(如像電影《武訓傳》及其它關于武訓的著作),就喪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則竟至向這種反動思想投降。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斗的共產黨,這難道不是事實嗎?”
七、江青組團調查武訓事件
據毛澤東貼身警衛李家驥回憶陪同江青組團赴山東調查武訓事件:
6月24日或25日,我們乘火車直奔濟南。江青、袁水拍、鐘惦都坐的軟臥。我不知道這個調查團誰是團長、副團長,但我能感到他們三人是核心人物,尤其是袁水拍更是公開的頭面人物,在公開場合江青叫李進,是工作人員。一到聊城,江青和袁水拍就召集會議研究工作。
在聊城下去調查是很辛苦的,步行十幾里路,不讓坐車。在郊區一個大村子,江青、袁水拍、鐘惦等和幾個老鄉嘮嗑。因我在場,聽到了一些談話內容:
“你多大年紀了?”江青問其中一位老人。
“八十多了。”
“給我們講講武訓辦義學的事好嗎?”
“那時我還小,但有印象。他各地都去,求爺爺、求奶奶地到處要錢、要飯,都是為了辦學。窮人太窮,沒人給他捐錢,富人有錢,有的給他一點,有的也不給。他也不容易,吃了一輩子苦。辦了學校,窮人的孩子還是念不起書,念得起書的還是富人家的孩子。”
“這里的老百姓怎么看武訓?”
“武訓不是為自己,他自己也沒得到什么。聽說皇上給他黃馬褂,他不要。雖然累了苦了一輩子,想為窮人辦點好事,窮人也沒沾著多少光。”
這一天調查團還去了一個地方,在一家跟老頭老太太談了挺長時間。他們夫婦都80歲了,老太太頭腦不清楚了,老頭腦子很好使,他介紹了很多很客觀的情況:“武訓確有這個人。武訓辦學,也確有這個事。武訓不容易,雖然他辦了幾所學校,有幾個窮人能念得起書,還是富人在那里念書。說來說去還是為富人服務,為統治階級服務,要不皇帝怎么給他黃馬褂。”
到了堂邑,調查團調查得更細,走的地方更多,大體上也是兩種觀點。
大概是7月18日回到北京。對于這次調查,江青始終情緒很高,回北京帶有凱旋的樣子。但由于過于勞累,回到北京的第三天就病倒了,她的膽囊炎犯了。江青和袁水拍向主席匯報了這次調查的詳細情況。主席對江青和調查團的工作是滿意的。匯報后江青就休息了,材料的最后修改、定稿都是袁水拍、鐘惦搞的。調查團寫了一個很長的《武訓歷史調查記》,據說這個材料主席親自修改,并在7月23日到28日發表在《人民日報》上,以后又出了小冊子。武訓歷史的調查和這個調查材料的發表,使討論(說批判更準確一些)掀起了新的高潮。
最后李家驥說,我對江青有三點印象:一是以普通工作人員出現,積極工作,沒搞特殊,吃派飯,與基層干部群眾打成一片,工作是深入細致的。二是江青身體不好,在農村工作20多天,很不容易。當時她因病容易出汗,尿頻尿急,有時找不到廁所,困難是可以想象的。我們當時擔心她挺不下來,結果還是堅持到了最后。三是與袁水拍等其他工作人員配合很好。對我們服務人員態度也比較好。總之,一切很順利。
一天在我值班時,主席對我說:“江青爭強好勝,身體不好,這次調查很順利,沒出大問題,她也挺了下來,多虧了你們幫助和照顧。”看來主席對江青在這次調查中的表現也是滿意的。
八、集體檢討:武訓“集封建反動落后勢力之大成”
毛澤東的社論發表之后,周恩來首先在黨中央為《武訓傳》的公映作了檢討。具體的檢討內容不得而知,但1952年周恩來在上海曾公開講過:“最近全國都在批判電影《武訓傳》,拍攝和放映《武訓傳》,我是點了頭的。因此我要承擔很大一部分責任,我已經向黨中央作了檢討,今天我在這個大會上再一次檢討。至于孫瑜同志和趙丹同志,他們都是做具體工作的,不應承擔主要責任。他們都是優秀的電影工作同志,昆侖電影公司也一直是在我們黨領導下的進步電影公司,拍過不少有影響的好電影。我祝愿他們總結經驗教訓,以后拍出更多好影片來。”由此似乎不難推測其檢討的具體內容。其他如朱德、夏衍等人也作了檢討。
黨外檢討最積極的當數郭沫若。在《人民日報》社論發表僅僅十天之后,6月1日,郭沫若寫出《聯系著武訓批判的自我檢討》,刊登在6月7日的《人民日報》上。郭認為自己犯了錯誤:“主要的原因是不曾從本質上去看武訓,而且把他孤立地看,更不曾把他和太平天國與捻軍的革命運動聯系起來看。今天武訓的本質被闡明了,武訓活動當時的農民革命的史實也昭示了出來,便十足證明武訓的落后、反動、甚至反革命了”;“武訓的以身作則的奴化教育,事實上是比奴化教育本身,尤其值得詛咒”。
江青經過大量實地調查的《武訓歷史調查記》出爐后,郭沫若根據《調查記》主旨,再度修正了自己對武訓的“認識”:“武訓倒真可以說是封建社會的一個結晶。他以一人之身而兼備了大流氓、大騙子、大地主、大債主、大名人、大善士、大偶像……真可謂集封建反動落后勢力之大成了。”郭沫若說,在讀了這篇《調查記》之后,“假使不是存心反動”,“誰不會瞠然自失而深刻檢討呢?”
比郭沫若更激進的批判者也是有的。上海《大公報》1951年6月8日刊蔡尚思的文章說:“武訓實集奴性、畜性之大成,不但違反了農民的性格,而且違反了人性;不但不像農民,而且不像人類。把武訓看作農民就侮辱了農民,把武訓看作人類就侮辱了人類。而且他連畜生都不如。”對于蔡的話,連中宣傳部都認為是“迎合潮流,信口開河。”(《〈武訓傳〉討論中的一些偏向》,*宣傳部編《宣傳通訊》,1951年5期,1951年6月) 。
教育界自然更是戰戰兢兢。紅色教育家徐特立說:“武訓所進行的教育是奴隸教育,是躺下來的教育,和我們今天的革命運動站起來的教育是尖銳對立的。……關于武訓的討論,是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是一個斗爭”;“(武訓的)苦行是反革命的苦行”;“不要只看到死武訓只有一個,而同情苦行的活武訓數量是太大了”。
國統區教育家馬敘倫檢討自己說:“武訓這個人我過去也曾經很著力地表揚過。……第二個原因……我就曾經進過武訓式的義塾。這種學校,這種教育,完全和百分之八、九十以上的工農大眾絕對沒有關系。……(出來的學生)只替反動統治階級效勞。……我過去對武訓的同情和表揚,實在是錯誤的。尤其是在解放戰爭勝利,人民掌握政權以后,我已經站在為人民服務的立場,并且還在領導全國的教育工作,卻還來盲目地表揚武訓,更是不可饒恕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