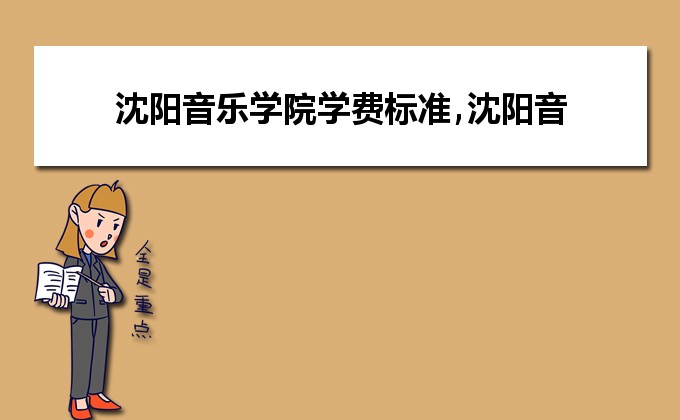《黑客帝國》三部曲從奴役和仇恨開始,首先講述的是猶太和基督教的歷史,是善和惡的完全對立,是上帝和撒旦你死我活的較量。下面是小編為您整理的觀后感,歡迎閱讀。
黑客帝國是我迄今為止看到的最具哲學意味的電影,讓我經(jīng)常一看再看。影片情節(jié)隨著一個個哲學難題快節(jié)奏地不斷鋪開,除了好萊塢精彩的動作設計、打斗場面和不斷涌現(xiàn)的俊男美女、酷裝奢物帶來的視覺享受外,最關鍵是那影片給我?guī)淼恼軐W思辨。哲學家們從中可以看到自己感興趣的哲學問題:存在主義,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佛教,后現(xiàn)代主義,隨便什么主義,你都能夠在《黑客帝國》中找到。這部電影不是隨意潑灑出來的一時靈感,在他的背后有一個明確的計劃并且是有意與哲學聯(lián)系在一起,影片中充斥著與哲學有關的重大命題以及暗示。因為電影中的哲學知識太廣太深,雖然精彩的電影劇情徐徐鋪開,但對于一般人來說,還是太晦澀難懂。
尼歐被什么是真實困擾著。莫斐斯告訴尼歐,他一生下來就活在一個心靈的牢籠之中。即使是監(jiān)獄里的囚徒,枷鎖下的奴隸,你可控制他的身體,但永遠無法控制他的思想。然而真正的危機在于你根本不知道自己生活在一個心靈的牢籠里,你的思想也被別人控制,因而你沒有要從那里逃離的強烈愿望,這無疑是最可悲的一件事。生活在這樣的桎梏里,即使被拯救心靈一樣是被捆綁著。柏拉圖的《理想國》中這樣描述,“假設他們中的一個人被解放了,被迫突然站起來,把頭轉過來,眼睛在燈光的照耀下活動;所有這些動作都將會是很痛苦的,他會感覺頭暈目眩而無法辨認出某些物體,雖然這些物體的影子他曾經(jīng)看到過。如果有人告訴他,他以前所看到的東西都是些毫無意義的幻覺,你認為他會說什么呢?但是現(xiàn)在,真實近在咫尺,他看到的是更加真實的物體,那么他會有一種更加真實的感覺嗎?……他不會感到困惑嗎?不會認為現(xiàn)在給他看的物體不可能像他以前看到的那樣真實么?”這種寓意剛好可以形容尼歐從母體中獲得解放時的困惑。洞穴里的囚犯們脖子上、手上以及腳上都戴著鐐銬,他們從一生下來就是這個樣子,因此他們對于其他的生活方式根本就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這些囚犯們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囚犯,他們不會懷疑,除了他們所經(jīng)歷的事情以外還有任何的真實。當然,尼歐的故事也與其相似,尼歐發(fā)現(xiàn)自己生活在囚禁中,或者更確切的說,發(fā)現(xiàn)自己被黑色的電纜線所束縛,電纜線刺激著母體產(chǎn)生幻覺。尼奧看到其他不知情的囚犯的情景時感到很驚駭,他們沉睡在有插孔的膠粘的粉紅色的洞穴夾層中,尼奧不想接受這個事實,即它現(xiàn)在所看到的是真實的,而在此之前,他一直生活在一個夢世界里,莫斐斯使尼奧相信:這些人中的大部分都還沒有做好準備被拯救。尼奧的恢復過程是痛苦不堪的。“為什么我的眼睛有些疼痛?”尼奧問道。“因為你從來沒有用過它們。”莫斐斯回答他說。
什么是真實,你如何定義真實?柏拉圖的寓言故事指出并鼓勵讀者們面向一個更高層次的現(xiàn)實。我們所有人就如同這些囚犯一樣,因為我們經(jīng)常錯誤地認為:我們所生活的現(xiàn)實就是存在著的最真實的最高層次的現(xiàn)實。我們在現(xiàn)實的水平上所經(jīng)歷的一切都是通過我們的五大器官所獲得的,他們只是對更高層次的現(xiàn)實可憐的模仿。我們可以聞到花香,聽見流水聲,觸摸到柔和的葉片。但是所有這些事情只不過是現(xiàn)實的模仿,只是復制品。視覺、嗅覺、聽覺、觸覺或其他什么感覺向你的大腦傳遞某些信息,你認為這些是真實的?我們只是在用感覺這種東西盡力為我們的大腦來模仿或形容這個現(xiàn)實的客觀物質世界。更高層次的現(xiàn)實怎樣才能為我們所知?理解的重要性不是通過感覺而是要通過智慧。墨菲斯告訴尼歐,沒有人會告訴你母體是什么。你必須親眼目睹。當然這不是字面上的視覺,而是一種能夠使你理解母體的直接的會意。尼歐也認識到智慧比感覺更加重要,因此湯匙根本不存在。柏拉圖認為智慧和身體是背道而馳的,人們在出生時這二者的錯誤結合造成了記憶的損失,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健忘癥。在去見墨菲斯的路上,尼歐曾考慮過退出,但是崔妮蒂的一句話促使尼歐改變心意。崔妮蒂說,“你活在這個虛擬的世界里,尼歐,對它很清楚,只有一個后果,我知道,那不是你想要的。”
我們大多數(shù)人都會想當然地以為,世界幾乎就像我們所看到、聽到的和感覺到的那樣存在著。在你看來,你躺在沙發(fā)上看電影,這就是現(xiàn)實的存在。你幾乎不會去懷疑它的真實性。然而重要的是,一旦對它表示懷疑,你就會看起來像一個神經(jīng)質,當然誰會對它提出質疑呢?
同樣,托馬斯?安德森認為自己是一個合格的公民,會幫助房東太太倒垃圾,同時在一家軟件公司上班。從這個層面上說,安德森對真實世界的篤信和我們都是一樣的,同時這就解釋了為什么對他而言,得知他生活的那個世界根本就不是真實存在的是如此痛苦。我們從電影中知道安德森平凡但是舒適的生存空間是由計算機系統(tǒng)操縱,系統(tǒng)在他的大腦里產(chǎn)生的一個虛擬制造的假象。人類在里面不斷地出生、成長和成熟,同時被用作更新的能量源泉。
正如莫斐斯向尼歐解釋的那樣,這個虛擬世界,也就是“母體”是無處不在的:它就在我們身邊,隨處可見。即使是現(xiàn)在,它就在這個房間里。你可以從窗戶外看到它,你打開電視的時候也能看到它。你上班的時候能感覺得到它,甚至是你上教堂時,納稅時也是一樣。它就是虛擬世界,在你眼前制造假象、蒙蔽視聽。尼歐,你是一個奴隸。像其他人一樣,你一生下來就注定要被奴役,一生下來就生活在一個沒有知覺的牢獄里,一個心靈的牢籠。安德森以及和他同時代的人都被欺騙了,他們錯誤地認為他們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可以自由的看報,看電視,沖澡。然而殘酷的真相卻是,他們只不過是被拘獲在小小的容器里,容器搜集他們的生物電能,分配給奴隸主似的計算機系統(tǒng)。當尼歐得知事情的真相時,他感到很不適應,難以接受,試圖回到他原先的在母體內(nèi)的生活,盡管那是虛假的。賽福發(fā)現(xiàn)真相后的情形更加嚴重,于是背叛莫斐斯以換取在母體內(nèi)過一種富有的、地位顯赫的然而是虛假的生活,這便是無知是福。《黑客帝國》在哲學界也引發(fā)了不小的騷動,一些哲學家們甚至聲稱,我們自己可能也被束縛在幻想世界里。
在哲學上,我們所看到、聽到和感覺到的世界可能是一種幻覺。懷疑論的擁護者們提出了這種假說。他們認為我們不可能確切地知道客觀世界的存在。因此,他們主張,對我們關于客觀世界的認識進行懷疑是有道理的。笛卡爾在《哲學沉思錄》中提出了一個頗具影響力的懷疑性論點,只有是絕對確定的那些信念才會通過笛卡爾的檢驗標準。只有這樣的信念才能夠成為科學可以真正依靠的基礎。因此。首先進入這種信念懸置過程的是笛卡爾在感覺的基礎上所形成的那些信念。我們認為自己通過視覺、聽覺、觸覺、嗅覺和味覺收集到的一些信息的觀點是正確的。例如,當我們看見同學在捧著書時,我們會想當然的認為他一定在用功看書。但是有時候,我們會發(fā)現(xiàn)感覺欺騙了我們。尤其是在觀看非常小或者是非常遠的物體時,我們更會被感覺所欺騙。但是,這種情況同樣也適用于其他物體。我們認為同學一定在看書,說不定此時他心猿意馬,期盼著下課鈴聲響起。由于我們的感覺有時候會欺騙我們,因而,我們建立在感覺基礎上的許多信念并不能夠滿足笛卡爾的高標準要求,因此他使得這些信念失去了應有的作用。笛卡爾進一步指出,當我們做夢的時候,可能在你看來,自已正坐在椅子上認真的看書,但實際上你正躺在床上酣睡。除非我們醒過來,否則我們無法分辨出自己是在看書還是在睡覺。
這是當尼歐提出疑問時莫斐斯加以確認的一種觀點:尼歐,你曾經(jīng)做過一種夢,在夢中你感覺是如此的真實么。要是你醒不過來怎么辦?你該如何分辨夢中的世界和真實的世界?笛卡爾在夢的論證的基礎上總結出一種觀點,就是:感官體驗是一種不可信賴的確證機制,因此他對于在感官證據(jù)的基礎上形成的所有信念都表示懷疑。
雖然關于夢的論證使我們有理由懷疑我們關于物質世界的看法是否正確,但或許大家會說,無論在現(xiàn)實還是夢中,我們都會相信,1+1=2,或者我們的母親是個女的等等,難道這個也要懷疑嗎?笛卡爾卻思考更為根本性的東西,在《沉思錄》中,笛卡爾假設“有一個法力無邊,狡猾無比的惡毒的魔鬼費盡心思地運用它所有的法力來欺騙我”,這個惡魔甚至可以更輕而易舉地誤導我們,它連1+1=2,母親是個女的,都可以改掉。惡魔直接改了我們的腦電波,讓我們腦袋里生成1+1=5,母親是男的等非主流現(xiàn)實,我們甚至不能說它是錯的,只是我們現(xiàn)在說它是錯的,假如我們存在于母體的話。而且這個惡魔甚至可以更輕而易舉地誤導我們,使我們錯誤地認為在我們之外還存在著一個物質世界,而實際上“天空,空氣,地球,顏色,形狀,聲音,以及所有的客觀事物只不過是夢中的幻象,是它早就制造出來用以影響我們的判斷力”。因而,笛卡爾推斷說,“我會認為自己沒有手或眼睛,或肉體,或血液,或感覺,但卻錯誤地相信我擁有這些東西”。我們很難想象如何說明我們的生活不是由一個惡毒的魔鬼所制造的假象。那些看過《黑客帝國》的人可能確實有理由懷疑,即我們認為的自己所過的有意義的生活實際上是由智能計算機系統(tǒng)植入我們大腦中的一種假象。
彼得?安格也是一名懷疑論立場的擁護者,他提出了另一種可能性,他認為欺騙我們的不是一個邪惡的魔鬼,而是一個邪惡的科學家。在我們的世界存在著書架,桌子以及此類的物體,這種共同的信念只不過是由一個邪惡的科學家在我們大腦里精心制造的一種假象,一個超級神經(jīng)專家,他運用電腦產(chǎn)生電子脈沖,然后轉化成電極強加于我們中樞神經(jīng)系統(tǒng)的相關部位上。運用這些電子脈沖來刺激我們的大腦,科學家欺騙了我們,使我們錯誤地認為存在者椅子和書箱等東西,事實上根本就不存在這些東西。在這一種假說下沒有人能夠確信不存在這樣一個利用電極欺騙我們邪惡科學家。同樣,你無法確信你真的是坐在椅子上,讀著這本書,因為你從來都無法深信不疑地知道你到底會不會受到一個惡毒的神經(jīng)專家的操縱或者是像母體一樣的計算機系統(tǒng)的操縱。進一步想象一下,我們的大腦通過外科手術身體分離出來,被放在裝滿了供給大腦營養(yǎng)的化學物質的容器里面。一個強大的計算機把電子脈沖傳送給我們的大腦,于是我們的大腦就會產(chǎn)生出幻想,比方說,我們在沙發(fā)上讀書。與此同時,我們被分離出來的大腦始終漂浮在科學家實驗室里的那些容器中。計算機程序足夠高級,能夠對我們的大腦試圖產(chǎn)生的“行為”做出適當?shù)姆答仭@纾愕拇竽X努力地想使你的身體從沙發(fā)上站起來,計算機可以提供適當?shù)拿}沖以確保你可以從椅子上站起來走到廚房去。這種情節(jié)明顯與電影《黑客帝國》里人們所面臨的情形很相似,人們是否會懷疑自己是不是處在這樣的一種困境之中呢,事實上沒有人能夠回答這個問題。
幸運的是,持非懷疑論的哲學家們對這些令人困惑的問題做出了許多有力的回答。首先,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指出,這些假定只是一種可能性,而且還是一種非常不太可能的可能性。我們不辭辛勞地去理解笛卡爾懷疑理論,這個事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提出了一種哲學上的特殊情況,即對一種可以達到科學的最高理想境界的探求。需牢記的是,對笛卡爾而言,我們不可能絕對地確定惡魔(或者是一個邪惡的計算機系統(tǒng))沒有利用我們的感官來欺騙我們,因此,笛卡爾論辯說,我們不能運用感官來論證我們關于知識的那些主張是正確的。
從哲學層面上而言,當我們正在檢驗支持或者反對懷疑論的論點的時候,一個最嚴格的標準是十分必要的。然而,從日常生活的層面上而言,它們太嚴格、太苛刻了。比如,如果同學問你的生日是什么時候時,你說生日這東西真的存在嗎,時間真的存在嗎,同學肯定會認為你瘋了。這是因為,在不同的層面上知識包含不同的標準。在某些哲學層面上,我們給知識施加非常嚴格和苛刻的標準是十分恰當?shù)摹T谌粘I畹膶用嫔希覀兪┮阅切┪覀儽容^熟悉的正常標準也同樣正確,這些標準最大限度上滿足了我們所共享的常識性的知識。在日常生活的層面上,我們確實知道我們在哪里,我們的生日是什么時候。因此,你的確知道關于你自己以及你周圍的世界的很多事情,你通過每天的經(jīng)歷獲得對某些事物的信念是真實的。你知道太陽從東邊升起,魚生活在水中。因此我們應該抵制笛卡爾的懷疑論設置的非常特殊的主張。進一步分析,我們能夠辨別夢里和醒著的時候的經(jīng)歷本身就設定我們已經(jīng)意識到這兩種經(jīng)歷以及兩者之間的差別。我們能夠很明顯的討論兩者之間的差別正是因為它們之間卻有不同,我們已經(jīng)意識到不同。由此可以得出結論,我們有足夠的理由來證明我們有關世界存在的知識,有關世界的本質和構成的知識都是正確的。
我們需要對賽福這個人物加以強調,他與史密斯進行了一場交易。賽佛明明知道母體不是真實的,但是他認為自己只要對真實的世界視而不見,他就能重新回到那個虛假的快樂世界中去。這是典型的享樂主義,快樂成了他活著的唯一理由。但是實際上,利用電極產(chǎn)生快樂的經(jīng)歷,只是讓我們看起來極其快樂而已。于是,諾齊克問道:“你愿意被插上插頭然后在機器里過這種生活嗎?”賽佛回答我愿意。但是我們大多數(shù)人會更加謹慎,把我們的生活交給電極刺激是否妥當。諾齊克用一系列觀點駁斥了向計算機屈服的人。他說:“我們想要去做某些事情,而不只是擁有做哪些事情的經(jīng)驗。”計算機系統(tǒng)不允許我們以任何形式與現(xiàn)實取得聯(lián)系,而不顧大多數(shù)人不得不這樣做的強烈愿望。我們意識到我們不會通過計算機機器來體驗生活,我們意識到經(jīng)驗之外有更重要的事情。
到底存不存在真實的世界,這的確是一個令人費解的問題,這正是《黑客帝國》這部電影讓我著迷的地方,不同的人從不同角度觀看這部電影,就會獲得不同的哲學體驗。這部電影中濃密的化不開的哲學思考,讓人對人生,世界有了不同以往的觀念,打破了我們的固有思考方式,電影也應當是這樣,讓人咀嚼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