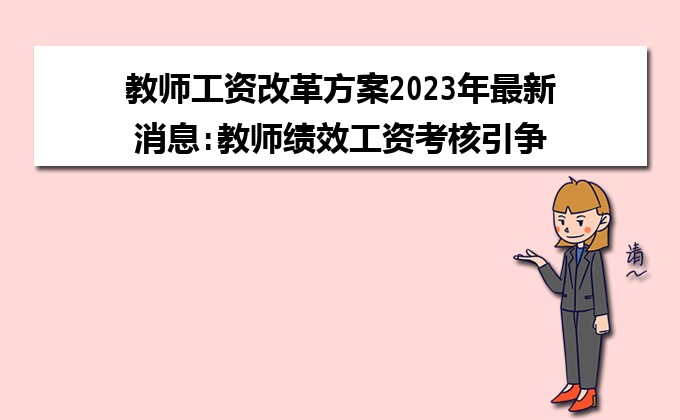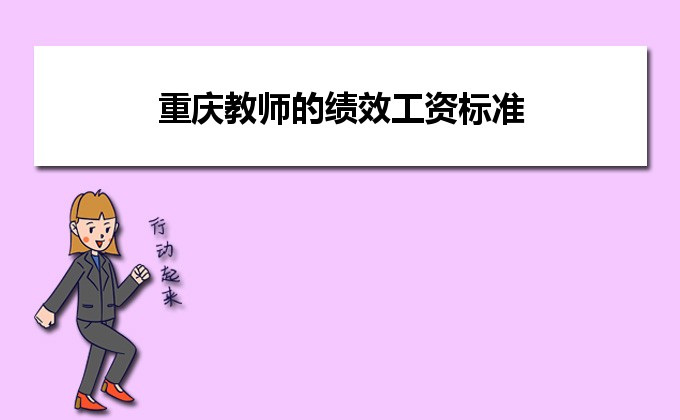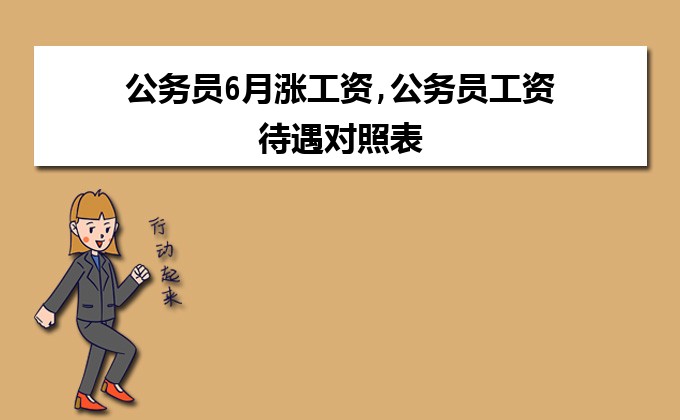績效工資體制的激勵效果在實際操作中未能發揮出來,薪酬發放的平均主義傾向普遍存在
改革使公辦教師與公務員之間以及公辦教師群體內部的工資收入差距逐步縮小,優質師資收入明顯下降
改革后學校的經費支配自主權普遍下降,教師收入的調節能力和激勵機制的設計能力被削弱
自2008年以來,伴隨著義務教育免費政策在城市和農村的全面實施,中央推行了教師績效工資制度改革,對教師的津補貼制度進行了規范,同時提高了公辦教師(特別是義務教育階段的教師)的工資待遇。
盡管這次改革對于規范基礎教育階段教師工資的標準、水平和結構產生了顯著作用,但其局限性也比較明顯。近年來,我和同事調研浙江、湖北、甘肅等十余省后發現:新體制建立6年間,一直無法建立正常的工資增長機制,教師的基本工資標準至始終沒有提高,教師工資收入的增長主要是依靠地方政府自行提高績效工資和津補貼水平。并且,績效工資體制的激勵效果在實際操作中未能發揮出來,薪酬發放的平均主義傾向普遍存在。
優秀教師收入為何下降
在分級辦學的時代,許多義務教育階段的學校都采取了各種與教師收入水平掛鉤的獎懲措施。這些獎懲措施的資金來源往往是學校的各種收費收入,而收費的水平取決于學校的辦學質量。
即便是農村學校也不例外。當時,一些教學表現優秀的農村學校可以通過招收大量擇校生來獲取事業性收入,于是,第一線教學骨干教師的津補貼和獎金收入可能會顯著高于基本工資收入。比如,2000年時湖北某縣一名優秀的農村初中教師骨干各種收入總和可達每月2500元,相當于當時鄉鎮公務員賬面工資的3倍。
伴隨著農村稅費體制改革、“以縣為主”以及農村免雜費政策的實施,國家連續多次提高了公務員和教師的基本工資標準,并強化了農村教師工資發放的財力保障機制。改革使公辦教師與公務員之間以及公辦教師群體內部的工資收入差距逐步縮小,然而優質師資的收入卻明顯下降。
2008年的改革啟動后,包括高中和中職在內的基礎教育階段學校的收費(或創收)政策都在日漸收緊,各級財政為學校所撥付的公用經費中一般也不容許給教師發放津補貼。與此同時,教師工資收入的城鄉差距被拉平,教師工資與公務員工資之間的硬性掛鉤機制被進一步強化。
然而,改革后學校的經費支配自主權卻普遍下降,對于教師收入的調節能力和激勵機制的設計能力嚴重削弱。一旦學校依賴財政撥款來進行獎懲,而撥款總額卻與學校的辦學質量無關,則獎懲制度在教師內部就難以執行了。一個可以觀察的現象是,工資體制越集權,教師群體的攀比效應越強,越難以把財政撥款與教學質量掛鉤。
激勵機制被嚴重虛化
現行體制下,教師工資主要由基本工資、績效工資以及津補貼三部分構成。雖然教師績效工資體制在啟動伊始就充分關注了教師激勵機制的重要性,但是相應的機制設計在現實執行中卻并不順暢。
改革之后,本應依據績效考核發放的獎勵性工資部分往往只能采取平均分配的方式,激勵機制被嚴重虛化。我們在走訪河南的一所中職學校時發現,該校教師的獎勵性績效工資按照績效考核結果分為三個等次發放,但是每個等次之間僅僅有10元錢的差距。“這主要是在名譽上對教師進行鼓勵。”該校校長強調。
一位黑龍江某縣的教育局局長在訪談中表示,“地方上完全按照國家政策來落實績效工資改革很困難,教師們不認可拿30%的績效工資進行二次分配,覺得這是拿自己的錢去給別人發獎金”。
我們在實地調查中發現,一些學校在對教師工資進行二次分配時,往往由于部分教師的抵制而流產,甚至得獎的教師迫于壓力也會主動退還獎金。特別是在同一個地區內部,當部分學校施行平均分配時,其他原本打算執行績效工資政策的學校也只能跟著一起搞平均主義。為此,部分地區的縣區政府把教師的績效工資集中起來,再根據考核結果進行統一發放,但卻引起全縣多個學校教師的集體抵制。
云南某縣的教育局局長在與我們交流中表現出了無奈的情緒:“最近教育局已經下文件要求各個學校不得對獎勵性績效工資進行二次分配,以免引起老師們的不滿。” 換言之,績效工資體制改革不僅未能有效調動教師工作的積極性,甚至反過來對教師群體的穩定帶來不利影響。
教師薪酬制度改革顯然不能僅僅著眼于提高教師群體的平均待遇水平,普漲工資并不等于教師工作積極性的提高。
教師薪酬體制改革能否適度分權
年初,中央政府著手對機關事業單位人員的薪酬體制進行新一輪的改革,公務員和教師的基本工資標準有所提高,社保體制并軌的改革也全面啟動。與此同時,地方政府較為普遍地提高了公務員和教師的津補貼水平。
在新一輪的教師薪酬體制改革中,建議決策部門不應繼續強化過往的政策思路,而有必要考慮對事業單位的薪酬制度進行市場化導向的改革,增加地方政府和基層單位的自主權以及工資水平調整的靈活度。
首先,基本工資標準管控權可以考慮以省級統籌體制為基礎向地方分權。同時,薪酬內部結構如基本工資與津補貼比例的調整權也下放到地方,并增強基層單位負責人對津補貼和獎金發放的自主權限。
在分權的架構下,中央政府的監管目標側重于對地區間的總體薪酬差距進行“限高、托低、穩中”的調控,并建立相應的獎懲機制。例如,如果某省部分縣市的教師工資水平與省會城市差距過大,則中央財政將扣減對于省級財政的轉移支付或者稅收返還,直接補助給相關縣市。
其次,教師與公務員工資的掛鉤機制在短期內很難取消,但可以做軟化處理,這需要通過增強基層事業單位的經費自主權來實現。第一,政府要區分哪些公共服務是基本公共服務,哪些不是,對于已經超出了政府財力保障范圍的公共服務,可以容許學校通過多渠道籌資來彌補財政投入的不足;第二,對于尚保留的學校收費項目(如高中階段的學費),應當賦予學校一定的自主定價權,以實現收費標準和學校教育質量之間的市場化關聯;第三,公辦學校對于公用經費和事業性收入應當具有一定自主支配權,用以對教師的收入進行微調。
一種觀點強調,公辦學校開設收費項目或者提高收費標準,將引起社會公眾的不滿情緒,誘發新的不穩定因素。而事實上,學校所面對的社會壓力主要是源于學校安全事件,而并非收費問題。從另一個角度上講,增強學校對于教師收入的調節能力和激勵機制設計能力,也可以扭轉“績效工資不績效”的被動局面,反而有利于減緩教師群體的不穩定因素。
最后,保留學校對于薪酬水平的微調權,也為上級行政部門從宏觀上調整工資標準提供了一扇觀測窗口,否則基于工資調查的正常增資機制很難操作。對于決策部門來說,調整基本工資和津補貼標準需要綜合考慮來自工資調查的市場信息以及基層單位的意見和訴求。學校對于教師收入的微調信息有助于決策部門判斷工資調標的真實壓力變化。比如,當課時津貼、班主任津貼的上浮頻率快于績效獎金,且類似現象在多個地區的學校同時出現時,就說明基層調薪的壓力在積累。
概括而言,建立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教師薪酬體制要把握十六字原則:中央調控、省級統籌、彈性管理、科學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