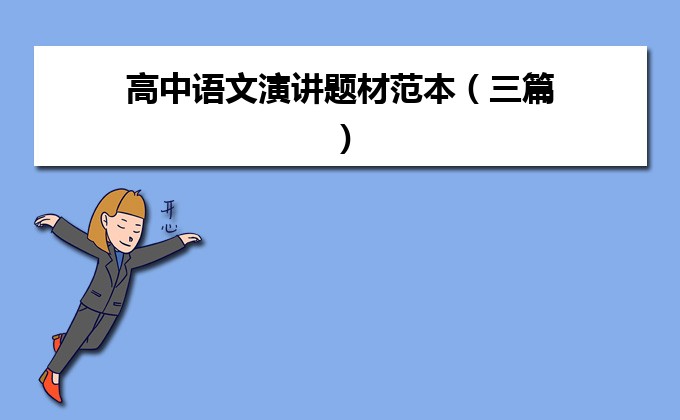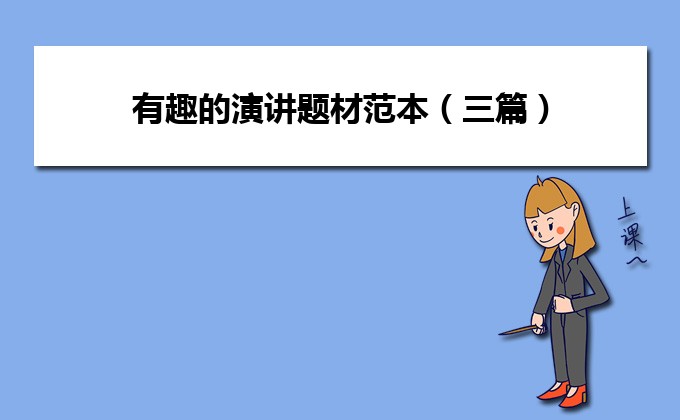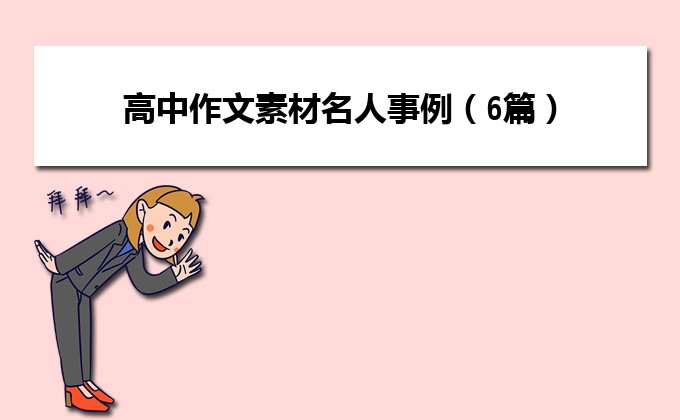有創意的課前演講稿篇一
那幾塊石墨,研出多少水墨年華;那幾滴墨色,恬淡了幾多蕭蕭往事。墨,淡漠,水墨,誰嘆蕭何,水墨色,幾點江南風景澈。??題記
我喜歡墨。而且格外的喜歡水墨丹青,莫名的偏愛揮毫書法,沒別的,僅僅,是喜歡。
我喜歡它什么呢?是喜歡淡淡水墨的交融?還是喜歡深淺不一的墨痕?或者喜歡若有若無的墨香?是了,卻都不是。我想,我最愛的僅僅是墨。
墨,是清淡的。墨,只有一種顏色。但這種顏色包含了太多顏色。沒錯,是黑色,萬千顏色交匯,這便凝成了黑,萬千黑色的交匯,這便成了墨。墨,多單純的色調,它并沒有西洋油彩的華麗和花哨,也沒有古埃及壁畫的神秘和莫測,僅僅,是墨。古代文人雅士,用墨畫天畫水畫葦塘,畫人畫物畫滄桑。寫景寫情寫惆悵,寫花寫月寫離殤。用水與墨的調配,絢爛出夢幻的景色,綻放出自己的心緒,鑄就震驚世界的千古絕唱。這一塊簡單的墨啊,經歷了幾千年歷史的變革,目睹了幾代人的興衰,又踏過幾次花落月缺的離合,才到了今天,凝成了墨。滴滴墨色寫往事,點點清痕紙上馳。墨,僅僅是墨。
墨,是神奇的。墨的醇香是在歲月的醞釀,和耐心的烘焙下,漾出的。沒有這兩樣,墨,便不是墨了,只是一塊比較離奇的石頭罷了。市場上賣的調好的墨汁,可還有昔日的芳香,別說歲月的醞釀了,就連磨,誰舍得浪費時間給你摸摸磨墨呢?打碎成粉再加入水即可。這“速成”的墨,外表沒有什么不同,但它的骨子里,可還有墨的執念與淡漠?這自來水,可有小池清泉的靈氣和甘甜?正統的墨,漸行漸遠,正漸漸消失在歷史的轉角。
倘若將一塊好墨,持手中,便有種莫名突兀的滿足,輕摁硯中,細細,緩緩,順時針研磨,覺得時光好像停止了,隨著墨在原地打轉而已。當你目睹著墨塊在手中,漾出別樣光華,墨汁漸漸濃郁,此時墨香便隨著這墨汁的流出而飄逸了。那一瞬間,在塵世的喧囂中,一定有一種“心遠地自偏”愜意的感覺注入四肢百骸。也許這便是水墨的魔力吧?誰說水墨無情?它也會看世間百態,也會品歲月如歌,如若你沒發現,那就只能怨你不懂墨。細細研磨調空靈,緩緩低吟世間情。墨,僅僅是墨嗎?
墨,是窈窕的。在寒冷的北方,簡單快捷的中性筆,水彩筆,油畫棒,隨處可見。相比這*妖媚洋氣的“嬌小姐”,墨,這樸實優雅的江南女子,實在不怎么受人注意,擠在小小的角落,陪著中國千年往事黯淡著追憶。只是偶爾幾位老者來看看,再搖頭嘆息著離去罷了。年輕的孩子,誰會注意這樣的“老古董”呢?可是,在南方,這本是窈窕的水土上,幾場春雨婆娑,水墨漸漸漫開,暈染出一片美麗的水墨丹青。畫既是景,景既是畫。不知是水墨丹青一朵朵開在江南這明媚的春光里,還是江南風景綻放在水墨中。窈窕著,震撼著人們的內心。水與墨,簡單的交匯,便氤氳出一派淡雅江南。水墨,水墨,僅僅是水與墨嗎?它寄托了多少愁思,幾多心事,花落迷離;它銘記了幾朝歷史,鐫刻了幾代江山,風過塵囂;它目睹了幾縷殘陽,留戀了幾簾幽夢,恬淡往事。輕觸素箋,起舞蹁躚,窈窕水墨,惹人空思念。思思怨怨孤舟泊,悲悲喜喜淡水墨。墨,不僅僅是墨。
墨,是飄逸的。狼毫筆幾番勾挑,如夢江南就呈現在小橋流水的宣紙上,靜靜的望著你。這水墨色并無簡筆速寫那般形象,也沒黑白素描那般的立體,還沒斑斕油畫那般的妖嬈,僅僅,呈現了寧靜恬淡的心境。速寫,素描,油畫,是可以臨摹的。但是,你可曾見過誰臨摹水墨畫的?有,那也只是學名家筆法,品名家底蘊罷了。水墨色,是一種氣,是一種發自內心的情感,是一種源于本真的吶喊。那磅礴心境,是常人學不來的。
我在看畫,看畫山清水秀,看畫云霧繚繞,畫亦在看我,看我本真心境,看我心中風景。那一汪水墨色,畫人,畫骨,畫心,那幾絲水墨痕,畫景,畫情,畫境。在塵世喧囂中,這水墨色恐怕是我等最后的幾寸精神凈土了。花花葉葉點相思,歲歲年年不了情。墨,僅僅是墨罷了。
墨香依舊,水仍清澈。但是一切,變了太多,太多。心中的水墨,故鄉的水墨,遠遠的,可望,不可即。墨,江南墨,水墨,花落驚蟄,水墨色,只字點秀額。唉,世俗喧囂中,真正的,我魂牽夢繞的水墨,難道只能在夢中重見了么?
有創意的課前演講稿篇二
哲學家康德說:“生氣,是拿別人的錯誤懲罰自己。”優雅的康德大概是不會有暴風驟雨的,心情永遠是天朗氣清。別人犯錯了,我們為此雷霆萬鈞,那犯錯的該是我們自己了。
現代的戴爾?卡內基不主張以牙還牙,他說:“要真正憎惡別人的簡單方法只有一個,即發揮對方的長處。”憎惡對方,狠不得食肉寢皮敲骨吸髓,結果只能使自己焦頭爛額,心力盡瘁。卡內基說的“憎惡”是另一種形式的“寬容”,憎惡別人不是咬牙切齒饕餮對手,而是吸取對方的長處化為自己強身壯體的鈣質。
狼再怎么扮演“慈祥的外婆”,發“從此吃素”的毒誓,也難改吃羊的本性,但如果捕殺凈盡,羊群反而容易產生瘟疫;兩虎共斗,其勢不俱生,但一旦英雄寂寞,不用關進柵欄,兇猛的老虎也會退化成病貓。把對手看做朋友,這是更高境界的寬容。
林肯總統對政敵素以寬容著稱,后來終于引起一議員的不滿,議員說:“你不應該試圖和那些人交朋友,而應該消滅他們。”林肯微笑著回答:“當他們變成我的朋友,難道我不正是在消滅我的敵人嗎?”一語中的,多一些寬容,公開的對手或許就是我們潛在的朋友。
三峽工程大江截流成功,誰對三峽工程的貢獻最大?著名的水利工程學家潘家錚這樣回答外國記者的提問:“那些反對三峽過程的人對三峽工程的貢獻最大。”反對者的存在,可讓保持清醒理智的頭腦,做事更周全;可激發你接受挑戰的勇氣,迸發出生命的潛能。這不是簡單的寬容,這寬容如硎,磨礪著你意志,磨亮了你生命的鋒芒。
雖然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有義務捍衛您說話的權利。這句話很多人都知道,它包含了寬容的民主性內核。良言一句三冬暖,寬容是冬天皚皚雪山上的暖陽;惡語傷人六月寒,如果你有了寬容之心,炎炎酷暑里就把它當作降溫的空調吧。
寬容是一種美。深邃的天空容忍了雷電風暴一時的肆虐,才有風和日麗;遼闊的大海容納了驚濤駭浪一時的猖獗,才有浩淼無垠;蒼莽的森林忍耐了弱肉強食一時的規律,才有郁郁蔥蔥。泰山不辭?土,方能成其高;江河不擇細流,方能成其大。寬容是壁立千仞的泰山,是容納百川的江河湖海。
與朋友交往,寬容是鮑叔牙多分給管仲的黃金。他不計較管仲的自私,也能理解管仲的貪生怕死,還向齊桓公推薦管仲做自己的上司。
與眾人交往,寬容是光武帝焚燒投敵信札的火炬。劉秀大敗王郎,攻入邯鄲,檢點前朝公文時,發現大量奉承王郎、侮罵劉秀甚至謀劃誅殺劉秀的信件。可劉秀對此視而不見,不顧眾臣反對,全部付之一炬。他不計前嫌,可化敵為友,壯大自己的力量,終成帝業。這把火,燒毀了嫌隙,也鑄煉堅固的事業之基。
你要寬容別人的齟齬、排擠甚至誣陷。因為你知道,正是你的力量讓對手恐慌。你更要知道,石縫里長出的草最能經受風雨。風涼話,正可以給你發熱的頭腦“冷敷”;給你穿的小鞋,或許能讓你在舞臺上跳出漫妙的“芭蕾舞”;給你的打擊,仿佛運動員手上的杠鈴,只會增加你的爆發力。睚眥必報,只能說明你無法虛懷若谷;言語刻薄,是一把雙刃劍,最終也割傷自己;以牙還牙,也只能說明你的“牙齒”很快要脫落了;血脈賁張,最容易引發“高血壓病”。“一只腳踩扁了紫羅蘭,它卻把香味留在那腳跟上,這就是寬恕。”安德魯?馬修斯在《寬容之心》中說了這樣一句能夠啟人心智的話。
有創意的課前演講稿篇三
茉莉是很江南的花。嬌小的笑靨中規中矩地托在細長的萼上,潔白的淺笑被叢叢的濃綠染上了流水一樣清新的色彩。茉莉是江南的碧玉,永遠那樣溫柔而怯弱地偎在枝頭,絕無牡丹醉臥或芍藥搔首的姿態。牡丹是洛陽城里的千金,芍藥呢,芍藥竟是個婀娜的戲子吧,慵妝的嬌癡媚態,水袖一甩,可以傾國。只有茉莉,是最江南的女子,白墻黛瓦的小院深處,也許在掀起最后一重湘簾才尋得見的深閨里,也許在那棵夜雨時會唱歌的芭蕉下,團扇后隱著的一彎淺笑,像江南的煙雨一樣氤氳在整個小鎮,雨季一樣靜謐。
茉莉的笑是可以傾城的。
“杏花春雨江南”,杏花是小白長紅越女的腮,茉莉是說吳儂軟語的蘇州女子。杏花在溪頭浣紗,茉莉在閨中刺繡。人說蘋果花是雪做的,梨花的瓣子是月亮做的,那茉莉是什么?茉莉的瓣,是四月的流水凝成的。唯有流水,才有那樣清澈而靈動,溶著仲春的碧色和煦暖的陽光。茉莉不是雨,雨是江南的病美人,是戴望舒愁結不展的丁香。
舒婷說不愿生女兒,因為女兒太嬌弱,太惹人愛憐,不忍將她帶到世上,對茉莉,也有這種感情吧。不敢養茉莉,江南的佳人畢竟不是黃土上摔打慣了的野丫頭,北方干澀的風一吹,水色的肌膚清癯了下去,豈不痛煞人哉!可喜愛茉莉不能忘懷,友人聞之,竟將家中長勢甚好的一盆慨然相贈,硬著頭皮捧回家,心中竟久懷著一種負罪感。為她騰出最明媚的窗口,每天敬畏地陪伴,卻不敢伸出手去褻瀆她翡翠色的裙擺??雖然她總是那樣淺淺地笑著。種茉莉的土是肥沃的黑色,不同于別的花盆里的黃土。那土在北方的花壇中隨處可見,長出的木槿竟也開得潑辣。效梁實秋于土中鉆小孔灌以芝麻漿湯,至于往花根下埋死貓的做法,只好望而卻步。剪枝的工作卻從不親自動手,因為不忍。
其實茉莉本不習慣于被這樣供著,在江南,她更多的時候只是陪襯。真真的,如古時的江南女子一樣。茉莉只是隨意地補在小園的角落里,或是靜默在一樹和田色的梔子下,香味流水一樣靜靜地縈繞著小城。
是的,茉莉的香氣永遠是那樣清雅而溫遜。“他年我若修花譜,列作人間第一香”,也許這并不是茉莉的本意。那第一的名號不妨讓給檀木,那種佛家厚重而機敏的感覺,靜坐參禪一樣的底蘊,偈語一樣的妙不可言。或者給了梅花吧,她開得夠辛苦了,暗香中竟也有些冰雪的味道。而茉莉,永遠只是深閨女子溫雅的氣息。
陸游說碾作了泥的梅花也是有香氣的,是不是這樣,我不敢說,但我知道和茶一起被水滾過的茉莉是不會失了香味的。北方的茶葉鋪子里,有南方的茉莉。北京人是鐘愛茉莉花茶的。茶葉一遍兩遍三遍地用茉莉窨過,臨賣時,伙計還會大方地抓上一把鮮茉莉包在一起。于是大大小小的茶葉鋪子里,各色的茶壺茶盞茶碗里,茉莉的氣息一齊彌散開。新茶上市的季節,茉莉傾城。可是這時的茉莉,也只是在陪襯著茶,就像在娘家時,斜插在秦淮女子的鬢梢,削減幾分牡丹的媚態,添一些閨中嫻靜的味道。茉莉是只能襯綠茶的,她托不起發酵過的釅茶。若是烏龍,還須嚼梅才好。黃山谷和蘇子瞻那次雅燕飛觴的茶會,想來作伴的該是梅花,茉莉是當不起的。
茉莉與梅花,細說來確有些緣分。入得歌的花木本就不多,至今還廣泛傳唱的更是有限,梅花是一,茉莉是一。《梅花三弄》是文人清絕的歌,《茉莉花》是吳地女子嫣然的巧笑。如果說梅花是塞北的士大夫,那么茉莉,不正是江南水邊素妝莞爾的傾城佳人?可是茉莉不會傾國,她不是胭脂堆成的西府海棠,她素面朝天,不愿爭什么,一如她的江南永遠甘心作中國文化的后院,她永遠是繡房里幾千年來都做著男人的陪襯的傾城女子。
茉莉傾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