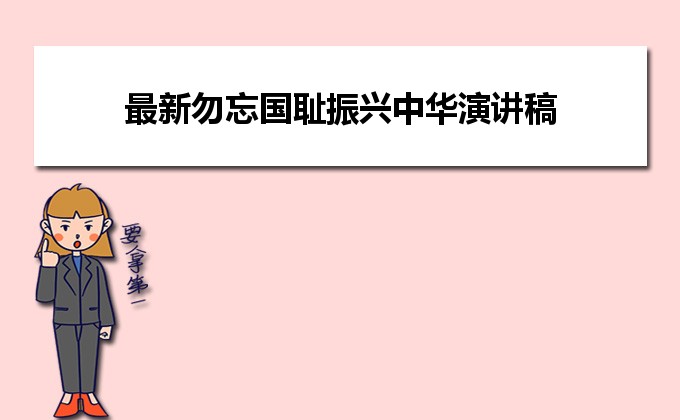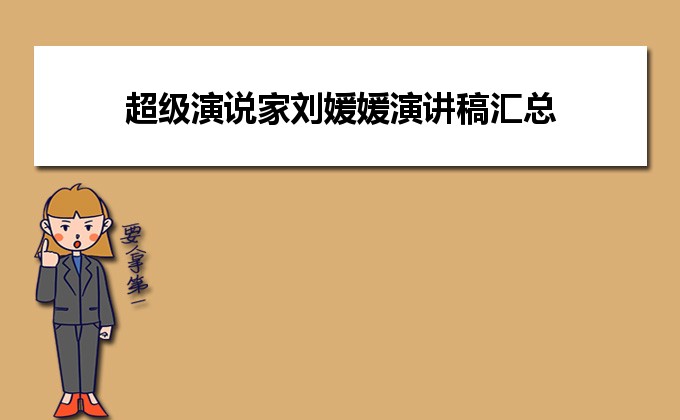我們都知道,生命在本質上是脆弱的,生老病死是每個人都逃脫不了的命運。但遺憾的是,我們既沒有選擇生的權利,也沒有選擇死的權利。
從2010年開始,我就長期與腫瘤病房結緣。腫瘤病房是我覺得待得最難受的地方,那是一個毫無生機的地方,我常常能看到光頭的、瘦骨嶙峋的、眼神完全空洞的病人,哭著說:讓我死去好了,讓我死去好了。
我的媽媽,就在那樣的地方,勇敢地與病魔作戰了兩年。媽媽去世前一個月,毫無防備的腦轉移,使她突然不再認得我,她只會喊著叫著,說痛。幾針嗎啡打下去,即便進入了淺昏迷狀態,她都仍然死死地咬著被子,甚至是手腳都被綁在病床上。那時候我心都要碎了。但令我更難過的,是媽媽大小便失禁的時候。她只要能有一絲清醒,能說一句話,哪怕都不知道我是誰,她說的話都是:“我能不能直接死掉。”我知道那是媽媽一生中最苦的時刻,一生中最沒有尊嚴的時刻。
無奈之下,在臨終病房里,我只能把止痛換成了比嗎啡藥效還要強80倍的芬太尼,那會使她看起來好受很多。而用上芬太尼的結果,就是導致深度昏迷。
深度昏迷的病人,幾乎屬于腦死亡的狀態,因為只靠輸液和能量維持生命,各個器官開始快速衰竭。在最后的時刻,病人會因為器官的衰竭導致無法呼吸,大口大口吸氣,然后停止呼吸,再大口大口吸氣,再停止。
那個過程,是家屬很難承受的。所以很多家屬都選擇在器官衰竭但尚有心跳的時候,選擇拔管。
我不想為媽媽做任何生死的決定,我希望她活著。但是現實就是,我必須為她做出我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為她做的決定。而那個決定,不是可以選擇她生,僅僅只是可以為她選擇臨終鎮痛方案,選擇是否臨終搶救,選擇是否拔管。
作為女兒,簽字畫押的那一刻,意味著我親手將最愛的媽媽送往死亡,這是一個死路一條的決定。我希望另一個世界,會讓她再無痛苦。
后來我常常會回想起媽媽那些痛苦的時刻,回想起她的淚水,我覺得比什么都苦。我不想經歷像媽媽那樣痛苦的過程,更不希望像媽媽那樣,到了最后時刻也沒留一句話給我,我有太多太多的遺憾。所以我更害怕的是,自己毫無意識地死去,我希望至少,能在最后時刻,能留一句話,給我的兒子。
說到這里,可能有的人會覺得我在鼓吹安樂死。但事實是,在今年年初,父親進了ICU重癥監護室,我做出的是另一種選擇。
那時候我在廣東,父親在湖北。當時醫生在電話里說:“如果現在插管,你爸爸或許有一線生機,但也很有可能因為插管太痛苦,在10分鐘之內就沒命了。如果不插管,不可能到明天。”
因為不想放棄一絲機會,所以我立刻做了插管的決定。第二天清早趕回老家,幸好他活著。而另一個跟他同時進了IUC的病人,當晚死于插管。這讓我非常的后怕。爸爸在經歷了86個小時的危險期后,蘇醒過來,我對他說的第一句話就是:“對不起。”
無論我對我的父母做出了怎樣的選擇,無論結果是生是死,我終身,都會為做出的選擇而內疚和痛苦,因為沒有一個人可以決定另外一個人的生死。所以,對于同樣逃脫不了生老病死的大多數人來說,我們或許終有一天,會面臨兩難的抉擇。
一方面,走向生命終點前的掙扎,讓很多人意識到有尊嚴的死去是多么的重要,就像因癌癥去世的著名乒乓球運動員莊則棟所呼吁的那樣,“能不能不要再做無謂、無可奈何的、痛苦的掙扎,使病人有尊嚴地加速離開?”
但另一方面,如果允許安樂死,那么無論從法律、醫學、倫理上,我們都很難去界定怎么樣的情況才算符合安樂死的標準,而且生命的價值可能從此無處安放。
我想很長時間之內,關于安樂死的爭論還會持續下去,我也給不出任何答案。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走向死亡過程中,我們所承受的痛苦,以及留下的遺憾。我希望,我們每個人都有機會去決定自己的命運。我們不應該等到病人已經失去作決定的能力時,才由家屬去做一個無論如何都會是錯誤的決定。
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能美好地積極地活著,包括我自己。但是,如果我有那么一天,活著已經不能再讓我感覺輕松愉快,我希望我能夠有選擇死的權利,我希望是自己去做人生中最后一個決定,一個會讓我和我的親人永不會后悔的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