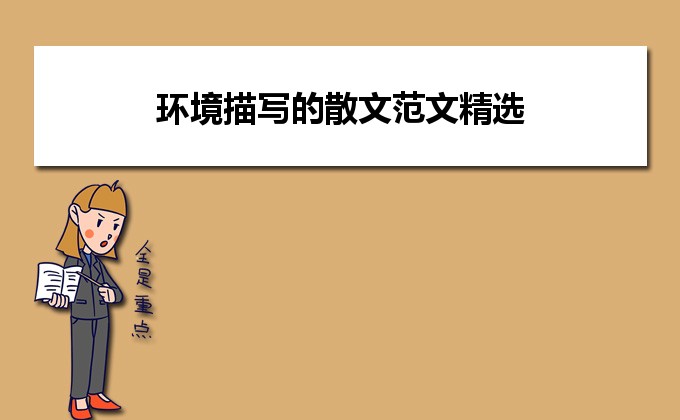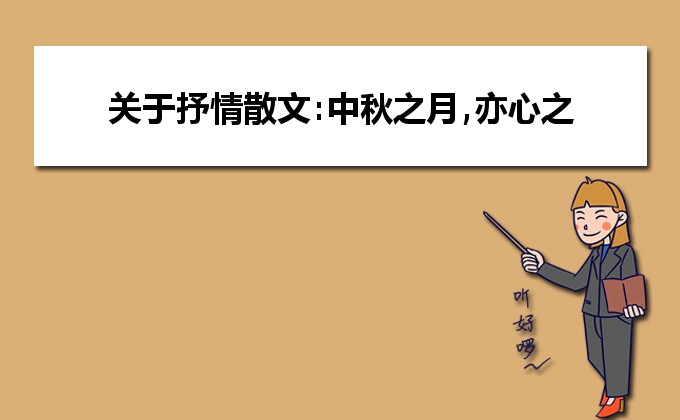在仲夏的某個陰雨天的傍晚,我們帶著一些憧憬,欣喜和淡淡的迷茫,第一次來到了我魂牽夢繞了三十年的西湖。從我孩童時起,我就讀過許多關于西湖的名篇,因此她在我心中也承載了我太多的期翼,太多的夢想。歷史的沉淀是如此的厚重,以至于我許多次從她身邊路過也不肯貿(mào)然前來。無數(shù)次的經(jīng)驗告訴我,夢想中的場景總是比現(xiàn)實中的要充沛而又空靈得多。淅淅瀝瀝的雨中,西湖就這樣在我眼前鋪展開來。岸柳回廊迎著風雨悄然相立,并沒有因為我這個遠道而來的游人表露出些許的驚喜。迷蒙的遠山在粼粼的波面那邊,蹲守著千百年來的某個姿勢,寂然無語。而那一抹長長的綠色絲帶,或許就是人們常說的白堤。漫步在岸邊,看著那密集的游船,我發(fā)現(xiàn)自己竟然沒有被西湖感動:躁動的塵世有太多的塵土掩遮了我的心靈,我已經(jīng)變得如此麻木和遲鈍。
混跡在來來往往的人群中,慢慢地一些若有若無的思緒在我腦海里時隱時現(xiàn)。也是在這樣的雨天嗎,白居易坐在哪棵樹下輕聲低吟那首穿越千年的詩篇?又是什么讓蘇東波流連忘返,佳句天成?吳歌晚唱,又是在哪一個雨天,許仙和他的娘子致命邂逅?浩淼的西湖水,真的都是白蛇的眼淚?或許千百年前我已經(jīng)來過此地,
那困頓的波瀾中也許還殘留著我當年遺失的一滴淚。可是,我究竟是在哪一個故事里失落的呢?漫長的歲月留下如此動人心魄的故事,而故事的主人卻不知身已何處。西湖的水一次一次洗刷著湖岸,仿佛在一次一次擦盡歲月的塵埃,不讓人們把那悠悠的往事遺忘。然而如織的游人又有幾許是來找尋那些消失了的悲歡離合,又有幾許人肯靜靜諦聽湖水深情的訴說與呢喃?他們頻繁地舉起相機,想要把自己擠進西湖的山水中,卻渾然不知,離開了人的靈性,得到的只是一些堆砌的色彩而已。沒有心靈的互動,山不過是高一點或矮一點的山,水不過是寬一點窄一點的水,岸也不過是直一點彎一點的岸而已。
天漸漸昏暗下來。一對戀人相擁在湖水邊。湖水把他們斑駁的身影揉搓著,展開著,仿佛要從哪些褶隙里找尋一些元素。湖水輕聲細語著,宛如在低問來人:若干年后,您們還會同來此地,回憶哪些溫馨的往事么?重拾哪些甜蜜的時光么?太多的舊事沉淪在湖水底下:她多少次看見海誓山盟的城墻在世俗的狂風暴雨中轟然坍塌,又多少次看見時間的利刃把謊言的羽毛一片片剝落。只有少數(shù)人碩果僅存,可是其中又有多少能再次同溫舊夢?岸邊的垂柳在涼爽的晚風中輕輕搖動長長的披發(fā),低頭不語。
第二天,我再次來到西湖邊,乘坐渡船去到湖中的三潭映月。陽光映照在湖面上,瀲滟的湖水宛如一幅巨幅的墨玉色綢緞在船底下飄曳。習習涼風掃走船頭夏天的郁熱,西湖美景撲面而來。熙熙攘攘的游人指指點點,兒童歡快的奔跑,和導游那喧鬧的擴音器,使人無法靜靜感悟什么。過多的游船來來往往把西湖切割成一段一段。假如東坡再世,再也無法吟誦出扣人心弦的詩歌。而漸漸在眼前放大的是法海的豐碑,那就是雷峰塔。其實許仙和白蛇并沒有干他什么事,但是法海有一沓沓規(guī)矩和典籍,他的一生就是以此為榮為生,假如逾越它們也能活的如此滋潤,那他豈不是白活人世了。如是在癡情的白蛇和正義的惡棍法海之間引發(fā)了一場災難性的沖突。終于,白蛇失去了她的許仙。千百年來,她靜靜躺在塔底,靜靜守望著她的愛情的家園。如今,法海的塔早就垮塌了,但她依然在那里久久守望。沒有了許仙,她的靈魂無處棲息,她只剩下這個家園了。可是,在這個日益追求膚淺的色彩和感官享受的世界里,有誰還能象她那樣無怨無悔的守望?西湖的水真是她孤獨的眼淚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