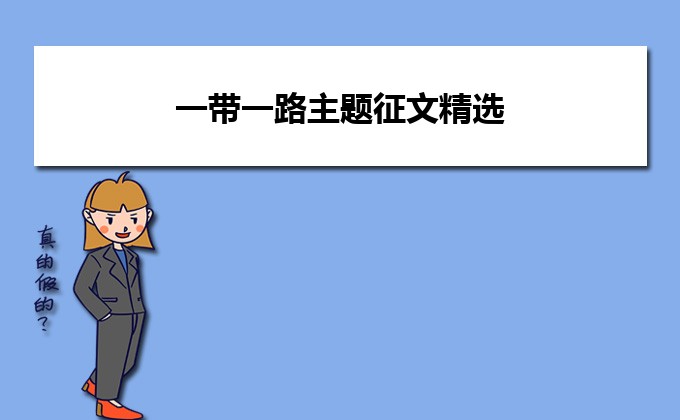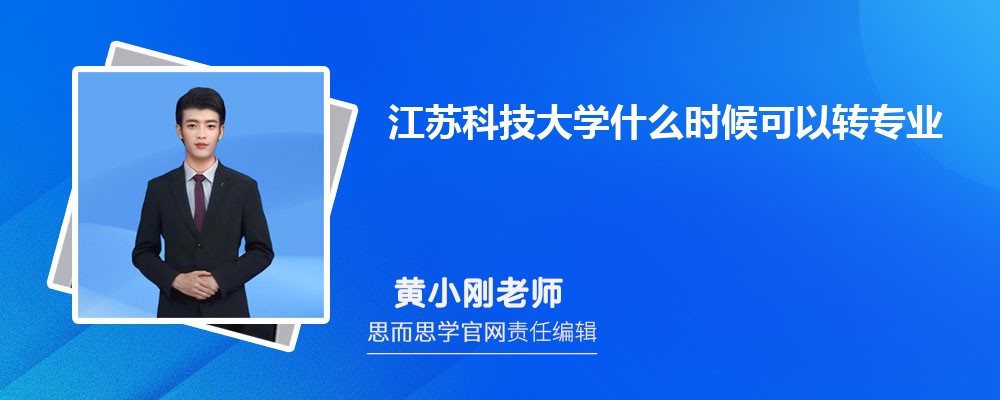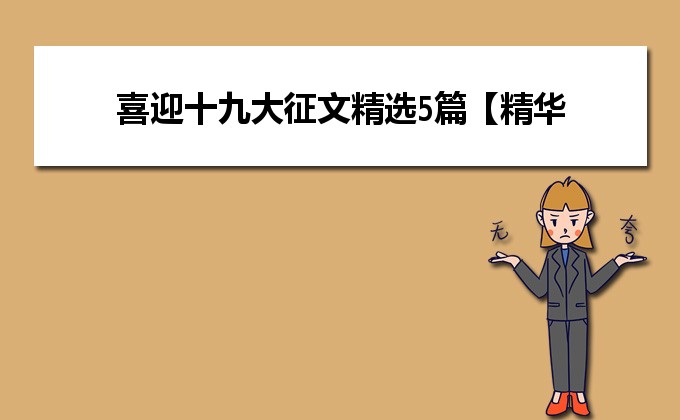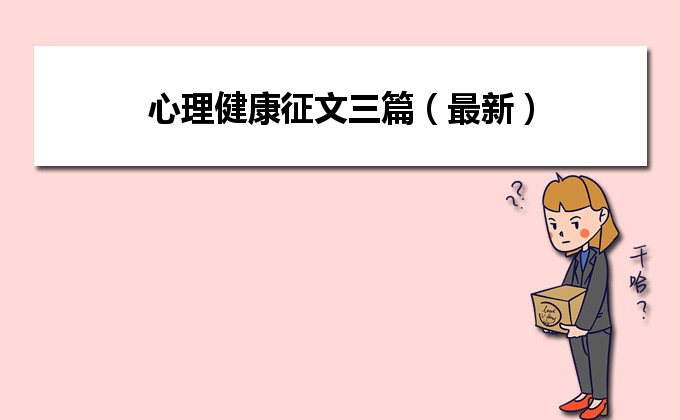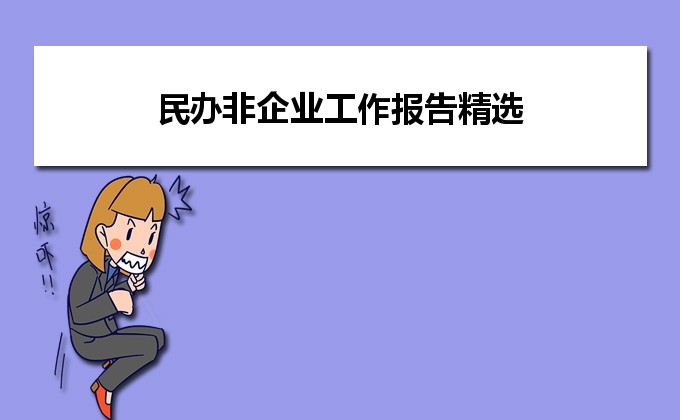一帶一路視野下的革命老區發展是怎么樣的呢?下面小編整理了一些一帶一路視野下的革命老區發展征文素材,供大家參考,希望對你們有幫助。
一帶一路視野下的革命老區發展征文素材
一、草原絲綢之路與“一帶一路”建設
“絲綢之路”除西域、南海路之外,還有一條歐亞草原路,早期輸入古希臘羅馬的中國絲綢,當主要是從這條路上西傳去的。一般認為,自西漢時起中西交通主要有兩條路線:一是經西域、中亞、西亞的陸路,即聞名中外的“絲綢之路”;一是自廣州出發由海上經東南亞諸國、印度的海路。也有人將兩者統你為絲綢之路,一為海上絲路,一為陸上絲路。
古代主要的中西交通路,除了人們所常提的南海路、西域路這兩條路線外,還有一條“歐亞草原路”。自古代起,由于地理環境關系,從蒙古高原直到中亞細亞,是游牧民族的主要生活區域。歷史上的絲綢之路經濟包含四條古通道。作為古絲綢之路四條通道之一的草原絲綢之路,是連接古代亞歐大陸的重要通道,是古絲綢之路的重要組成部分,曾經對東西方之間的商貿、文化交流發揮了重要作用。
2013年9月和10月,在訪問哈薩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亞時分別提出了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構想,并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得到進一步明確。在11月召開的APEC峰會期間,中國政府發起建設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絲路基金使得“一帶一路”在亞洲各國逐漸達成共識。“一帶一路”建設的再度興起,是國家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的全新戰略構想,也是構筑新時期國家戰略安全體系的重要內容。“一帶一路”建設并不僅僅是傳統意義上的通道建設,而是旨在通過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的“互通互聯”,構建起一個緊密聯系、活躍共生的大經濟區。一方面將實現與國內相關區域經濟發展戰略的對接,為沿線省份和地區帶來新的發展機遇,縮小區域差距,推動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另一方面將促進亞太經濟圈與歐洲經濟圈的溝通,將亞歐大陸打造成潛力巨大的經濟發展走廊。我國提出“一帶一路”發展戰略,其核心就是要進一步深化沿線區域合作共贏、推動沿線地區共同繁榮發展。草原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位于“一帶一路”的北端,是連接中國內地和俄羅斯、蒙古及歐洲腹地的重要節點。內蒙古地處我國正北方,在“一帶一路”戰略以及中俄蒙經濟走廊建設中占據特殊重要地位。作為國家向北開放的橋頭堡和中俄蒙經濟走廊建設節點省份,在加快建設整個“一帶一路”建設的時代背景下,內蒙古自治區的地位和作用也被賦予更多的含義和任務。
“一帶一路”建設的實施,給我國跨界民族的發展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我國與14個國家接壤,有陸地邊界線2.2萬公里,其中1.9萬多公里在少數民族地區,全國有34個民族跨境而居,總人口約為6600萬人”。“在當今世界上,像這樣同一個民族生活在若干國家,一個國家包括若干民族的現象相當普遍。作為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這些跨境民族分屬于不同的國家,卻有著共同的血緣文化聯系,民族同宗、文化同流、信仰大體相同”。跨界民族與周邊國家長期以來進行密切的經濟、文化交流,為加快發展我國與周邊國家的經貿文化交流與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一帶一路”經濟圈“覆蓋約44億人口,經濟總量約21萬億美元,分別占全球的63%和29%”。龐大的經貿交流關系將有助于促進區域內國家之間的文化交流與民間交往。內蒙古自治區的主體民族蒙古族是跨境民族,在“一帶一路”建設中具有獨特的優越性。在“一帶一路”建設中可以發揮居住在國境兩側“跨境民族”在人文歷史紐帶和民族文化認同方面的優勢,“提升邊境省區對境外國家的經濟和文化影響力,發展跨境貿易和勞務輸出,振興我國邊境省區經濟”。國境兩邊居住的人群,“在祖先血緣、語言宗教、文化傳統方面來說有可能具有相同特征”。
以錫林郭勒盟的蒙古族為例,位于內蒙古自治區中部,與京津冀經濟圈最近的錫林郭勒牧區,“擁有中蒙邊境線1103公里,與天津港、曹妃甸港約為400公里,錦州港、綏中港約550公里,是國家“一帶一路”戰略建設的重要輻射區。錫林郭勒盟地緣和文化優勢是向北開放的重要支撐,國際性常年開放的二連浩特和朱恩嘎達布其口岸將成為陸港經濟帶和中蒙俄經濟走廊中心區,也是歐亞經濟板塊的中樞鏈接點,跨境經濟合作將成為口岸發展的強勁動力”。錫林郭勒盟與蒙古國山水相連,與蒙古國南部、東部省區交往源遠流長,蒙古族同根同祖,語言文化相通,民族風俗相同,人民感情深厚。錫林郭勒盟地緣和文化優勢為深化中蒙合作、促進向北開放形成了長期穩定和獨特有力的支撐。主動融入“一帶一路”建設,充分利用蒙古族這一跨境民族優勢,積極推進與蒙古國的經濟、文化交流,加快建設與蒙古國公路鐵路互聯互通,不斷加強與蒙古國多領域合作是錫林郭勒牧區構建創新型、開放型經濟格局的重要途徑。
“一帶一路”建設為中蒙兩國的經濟發展和人文交流創造了良好的國際環境和機遇,拓展了草原絲綢之路的經濟文化內涵,草原絲綢之路沿線積淀豐厚的歷史遺產和宗教文化,正在成為“一帶一路”建設的文化基石和人文資源。學術界認為,“一帶一路”的建設“是個非常復雜的系統工程,尤其歷史的積淀和當今的處境,既是政治經濟戰略的范疇,也是文化戰略的領域,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對其宗教情況的了解和評估。我們回顧宗教沿絲綢之路進入中國的史實,正是提醒人們這些宗教在古今處境中都會對中國產生重要影響,值得我們高度重視”。應該“把宗教力作為我國對外發展戰略中一種特殊形態的文化軟實力,發揮它在對外發展戰略中的特殊作用”。
蒙古族作為跨界民族,擁有雙重文化背景,既熟悉中國文化,又熟知蒙古國的文化。有效利用好蒙古民族的宗教文化資源,將有助于進一步促進我國與蒙古國的全面交流,促進中國文化走出去。蒙古民族的宗教文化在中蒙文化交流中可以起到積極的文化中介作用。
二、中蒙宗教文化交流的歷史淵源與當下進展
中國明朝之際,藏傳佛教傳入蒙古地區。蒙古地區藏傳佛教的后弘期主要始自俺達汗時期,“藏傳佛教在蒙古地區的再度興起, 由于土默特阿勒坦汗西征青海和藏土及南征明朝, 再次接續了中斷二百余年的蒙古與西藏的緊密關系。”由于清政府一系的列扶持政策, 蒙藏地區形成達賴喇嘛、班禪、哲布尊丹巴、章嘉呼圖克圖成為黃教最大的四大活佛系統。正是在清王朝的特意提倡和保護下, 格魯派的影響深入到蒙古地區,滲透到蒙古族文化的各個領域。
1586年由外喀爾喀土謝圖汗、阿巴岱汗在哈喇和林(蒙古汗國古都)建成額爾德尼召,“這是現今蒙古國領土內的第一座喇嘛廟,其寺院面積為O.16平方公里,正方形,四周土圍墻上有90個佛塔。寺院建成一年后,招收了第一批喇嘛。阿巴岱汗皈依喇嘛教后,曾經親自朝見達賴喇嘛三世。此后,喇嘛教開始在蒙古地區流行起來”。現在,額爾德尼召已被列為博物館,是蒙古國重要的歷史古跡,仍是香火不斷。
現代蒙古國居民的宗教信仰曾經歷了曲折的過程。蒙古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后,包括藏傳佛教在內的宗教活動,在蘇聯實施的宗教政策的影響下,曾長期被取締和禁止,很多寺廟也遭受損毀。甘丹寺雖因其歷史文化價值而得以保留,并在1950年列為博物館,但不許舉行宗教活動。1985年以后,隨著蘇聯實行“新思維”改革,蒙古國內的宗教活動逐步得到恢復,其中包括修復滿茲召等寺廟,甘丹寺也重新成為重要的宗教活動場所。
自2013年中蒙兩國簽署《中蒙戰略伙伴關系中長期發展綱要》以來,中蒙兩國間的人文交流也日益頻繁。以宗教文化的交流為例,6月13日雍和宮向蒙古國捐贈彌勒佛像儀式在烏蘭巴托舉行。中國駐蒙古國大使王小龍在致辭中表示,“此次彌勒大佛捐贈及迎請儀式,是兩國宗教界的盛事,不僅密切了兩國宗教界的聯系,更為兩國人民友好交往打下了堅實的基礎”。2015年7月16日至18日,應中國佛教協會邀請,以蒙古國佛教協會會長達木丁蘇倫•納策格道爾吉為團長的蒙古國佛教代表團一行8人到內蒙古參訪交流。“達木丁蘇倫•納策格道爾吉對內蒙古佛教協會的熱情接待表示感謝。他表示,十分欽佩中國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此次蒙古國佛教代表團來內蒙古訪問意義重大,為中蒙佛教界在未來廣泛交流搭建了友好往來的平臺。蒙古國與內蒙古不僅是朋友,還是親戚,希望蒙古國與內蒙古佛教界加強交流合作,不斷增進中蒙兩國佛教四眾弟子的友誼,為弘法利生作出不懈努力。”
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組織的中國藏文化交流團于8月21日至23日訪問蒙古國。訪問期間,交流團在蒙古國首都烏蘭巴托同蒙古國媒體代表、國立大學、科學院專家及當地藏傳佛教界人士進行了深入交流,向各界介紹和闡釋了中國西藏經濟、社會、文化發展成就和民族宗教政策,全國宗教工作會議的重要精神,中國根據自己國情和西藏特點保護、傳承西藏文化的成功做法。蒙方對交流團介紹的信息表現出濃厚興趣,表達了進一步交流合作的愿望,并希望有機會到西藏參觀訪問。交流團團長、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所長王延中表示,蒙古國是“一帶一路”沿線的重要國家,“中蒙在文化和宗教等領域有著廣泛的聯系,繼續開展宗教等人文領域的交流,有利于加強中蒙雙方的互相理解,有利于深化兩國友好關系”。蒙古國佛教協會主席那策克道爾吉說:“蒙中在佛教文化上有很多共通點,兩國在佛教領域有著廣泛的交流合作空間,反對一些個人為了私利打著宗教的旗號從事干涉政治、破壞和平的行為”。蒙古國達希喬依倫寺住持、世界佛教協會副主席丹巴扎布表示,自己親自去過西藏,“了解西藏的宗教政策。這些政策是完全合理的,國家之間應該相互尊重,反對西方國家一些不負責任的涉藏言論”。可見,此次中國藏文化交流團訪問蒙古國對宣傳我國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同時在涉藏問題上征得有利于我國的國際話語權起到了重要作用。
9月26日,邢海明大使會見了正在蒙古訪問的中國佛教協會代表團一行。代表團由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趙九九任團長,團員還包括山西五臺山、甘肅拉卜楞寺、內蒙古呼和浩特大昭寺、藏語系高級佛學院等多位高僧。趙九九介紹了訪問有關情況。邢海明大使表示“當前中蒙關系發展順利,兩國高層交往密切,雙邊關系正處于歷史最好時期。加強中蒙人文交流是兩國元首達成的重要共識,宗教交流是人文交流的重要組成部分,希望中國佛協代表團以此訪為契機,進一步增強中蒙佛教界間的友誼,增進兩國人民相互理解,為促進中蒙關系發展作出積極貢獻”。趙九九團長表示“宗教交流對促進人文交往具有積極意義。中國佛教協會代表團將與蒙古佛教界深入交流,加深彼此間了解,增進兩國宗教界及民眾間感情,為中蒙關系增磚添瓦”。
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蒙古國在涉藏問題上具有特殊重要性,我們一定要高度重視蒙古國政界和宗教界在涉藏問題、達賴集團方面的輿情、言論和活動動態。達賴從1979年開始前后9次訪問蒙古國。十四世達賴“竄訪”蒙古國對中蒙關系產生了一些負面影響。據媒體報道“近日,蒙方不顧中方多次勸阻,執意邀請十四世達賴竄訪蒙古,中方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這次達賴竄訪蒙古國的過程中,甘丹寺發揮了重要作用。甘丹寺位于烏蘭巴托市西北郊的山丘上。始建于1664年,原是一個可移動的小型廟宇,到1838年擴建為蒙古地區的一個佛教中心,它由五座寺廟組成,寺周圍砌有磚墻,設南、西、東三個門,構成了一個龐大的古建筑群。由于最后四代哲布尊丹巴的府邸都設在這里,甘登寺成為蒙古政教關系史的見證者。現在甘丹寺仍為蒙古國佛教活動中心。20世紀90年代以后,蒙古社會變遷中的重要特點之一即是藏傳佛教的復興。其中甘丹寺成為當代蒙古國最重要的宗教場所,也是重要的宗教名勝古跡之一。
目前,蒙古國內香火最旺盛的寺廟就是甘丹寺(即庫侖伊克召),它是蒙古國內最大的佛教寺廟。十四世達賴“竄訪”蒙古國期間甘丹寺扮演了重要角色。我們應高度重視甘登寺在蒙古國的特殊地位和作用,通過一些積極主動的宗教文化交流和公共外交途徑,加強中蒙佛教界之間的交流、溝通和對話,有效消除十四世達賴“竄訪”蒙古國對我國所產生的負面消極影響。當下,對我國來說開展以達賴“竄訪”蒙古國這一問題為主題,規避今后宗教風險為目標的中蒙預防性外交是很有必要的。
三、“一帶一路”視野下的中蒙宗教文化交流愿景
蒙古國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一,“一帶一路”建設“可以與蒙古國正推動的諸多政策改革實現有效對接,中蒙兩國可在諸多具體領域開展務實和深度合作”。2013年10月,中蒙兩國簽署了《中蒙戰略伙伴關系中長期發展綱要》;8月22日晚,結束了對蒙古國為期兩天的國事訪問后回到北京。*主席此次“走親戚式”訪問有劃時代意義,“為中蒙關系今后發展繪制了新藍圖,必將進一步推進兩國在政治、經濟、人文等各方面合作,對兩國關系未來產生直接、深遠的影響”。8月,兩國聯合發布了《中蒙關于建立和發展全面戰略伙伴關系的聯合宣言》。兩大綱領性文件明確提出,雙方將“全面提升中蒙務實合作的規模、質量和水平。”目前,中蒙戰略伙伴關系的歷史積淀和現實基礎已具備。
在“一帶一路”建設框架下提出的中蒙俄經濟走廊建設,是中國政府結合三國合作發展空間巨大的現實狀況所提出的重要構想,旨在通過絲綢之路經濟帶、俄羅斯跨歐亞大鐵路、蒙古國草原之路的對接,打造一條貫通三國、橫跨亞歐大陸的合作新通道,為各國共同發展搭建新平臺。在中蒙俄經濟走廊建設中,蒙古國的“橋梁作用”舉足輕重。9月11日,同俄羅斯總統普京、蒙古國總統額勒貝格道爾吉舉行中俄蒙三國元首首次會晤,提出把絲綢之路經濟帶同俄羅斯跨歐亞大鐵路、蒙古國草原之路進行對接,共同打造中蒙俄經濟走廊的倡議。2015年7月9日,中國同俄羅斯總統普京、蒙古國總統額勒貝格道爾吉舉行中俄蒙元首第二次會晤,就將中方絲綢之路經濟帶倡議、蒙方“草原之路”倡議、俄方跨歐亞運輸大通道倡議進行對接達成重要共識,批準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俄羅斯聯邦、蒙古國發展三方合作中期路線圖》。“啟動中蒙俄經濟走廊建設是三國發展戰略高度契合的結果”。目前,中蒙關系已提升至“全面戰略伙伴關系”,這明確了兩國合作的發展方向,為中蒙兩國全面合作打下了政治互信基礎和制度建設基礎。
對中蒙兩國間的人文交流而言,宗教文化占據重要地位。由于藏傳佛教格魯派為蒙古國的國教,其重要性更為突出。蒙古國居民中,約有90%以上信奉藏傳佛教;信仰伊斯蘭教的穆斯林約占人口的4%。20世紀90年代以來,蒙古國的藏傳佛教呈復興之勢。蒙古國憲法第九條規定:在蒙古國,國家尊重宗教,宗教祟尚國家。為更好地協調國家與宗教的關系,蒙古國于1993年頒布《國家與寺廟關系法》。該法規定藏傳佛教為國教,同時聲明:信仰或不信仰任何宗教屬于個人的信念,禁止從事將公民按宗教信仰不同,或是以信仰或不信仰宗教進行排斥、歧視和分化的活動。這就從法律上保障了居民的宗教信仰自由。該法第四條還規定:國家從崇尚蒙古國人民的和睦和文化歷史傳統出發,尊重佛教在蒙古國的主導地位,但這并不妨礙公民信仰其他宗教。這一條款雖然引起了一些新傳入蒙古國的宗教如基督教派的不滿,但與佛教和平相處多年的蒙古國內的伊斯蘭教信徒并沒有提出質疑。在蒙古國,現有多種宗教,佛教和伊斯蘭教屬于蒙古國的傳統宗教,而20世紀90年代之后傳入蒙古國的宗教屬于非傳統宗教。目前的宗教矛盾主要表現在傳統宗教與非傳統宗教之間。
在“一帶一路”戰略背景下,國家層面上開始重視公共外交的重要性。中國公共外交要以中華文化歷史悠久、能量強大的宗教為資源,傳播中國智慧、講述中國故事、發出中國聲音,使中國公共外交更加有聲有色、深入人心。宗教是地緣政治中“貌不驚人”的軟實力,宗教發展現狀是公共外交的重要內容。在開展公共外交時要關注宗教的地緣政治影響。在全球化背景下,宗教外交越來越受到重視。宗教外交,又稱神?外交,簡單地講,就是一種“以信仰為基礎的外交”或是宗教在國際關系中的互動,即以宗教價值觀,追求一種宗教關懷或宗教目的并在其中有意識地因應自身國家利益的外交形態。目前,中國學界對宗教外交的權威定義是“宗教外交系指一個國家的中央政府以特定的宗教價值觀念為指導,通過職業外交官直接實施、授權或者委托各種宗教組織實施的外交行為以及默許宗教組織開展的針對另一個國家政府的游說活動。”這一定義中包括了宗教外交的主體(具有濃厚的政治考慮)、客體(宗教組織或教民)、目的(促進宗教“福音”的傳揚以及國家利益的實現)等。在當今全球化與碎片化比翼齊飛的態勢下“宗教外交作為一國政府打國際牌獲取政權合法性和支持度的工具,以及構建國家軟實力的重要舉措,勢將方興未艾”。著名學者卓新平在《關于宗教與文化戰略關系的思考》一文中提出“我們在當今錯綜復雜的世界局勢中要想守住人類可能共存的底線,使宗教爭取在世界和平中發揮其建設性功能,起到更為積極的作用,就必須解放思想,調整思路,做到整體思維、涵攝兼容”。
在今后的中蒙兩國交流中,中國公共外交需要借助藏傳佛教有效促進中蒙關系。中國外交既要重視與蒙古國政府的交流和合作,還要研究蒙古國社會中宗教的地位和作用,通過宗教資源開展公共外交,為拓展中蒙雙邊關系創造條件。
中蒙兩國間歷史上形成的民族和宗教淵源難以完全分割。發揮宗教的“親緣”作用,中蒙兩國間開展人文交流和民間公共外交很有必要。以地緣關系、親緣關系為紐帶的跨境民族可以成為宗教力的民間外交主體。中蒙兩國間歷史上形成的宗教跨境傳播,跨地域發展的平臺,可稱為當下中蒙兩國間積極開展多渠道公共外交的國際性平臺。
最近內蒙古自治區已確定向北開放戰略,在未來幾年,內蒙古自治區將貫徹落實國家“一帶一路”和向北開放戰略,加快與俄蒙互聯互通公路通道建設,對俄蒙將重點推進兩條出海通道、三條能源通道和三條旅游通道建設。在建設“一帶一路”和實施向北開放戰略進程中,我們應當堅持文化先行,通過進一步深化與蒙古國的文化交流與合作,促進兩國間區域合作,實現共同發展,讓命運共同體意識在沿線國家落地生根。文化的影響力超越時空,跨越國界。文化交流是民心工程、未來工程,潛移默化、潤物無聲。我們在建設“一帶一路”和實施向北開放戰略進程中,要積極發揮文化的橋梁作用和引領作用,加強中蒙兩國間各領域、各階層、各宗教信仰的交流交往,努力實現兩國的全方位交流與合作。其中,應重點挖掘和開發佛教文化資源,開展中蒙人文交流和民間公共外交活動。這有助于夯實我國同蒙古國合作的民意基礎。跨境民族文化的傳播容易形成地緣文化的認同。兩國關系親不親,關鍵在于民心。民心的親近無疑將對國家之間的外交、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領域產生顯著影響。佛教的慈悲、智慧、平等觀念,在信奉佛教的民眾占大多數的國家之間,能夠引起的共鳴則尤為廣泛與深入。由于民心的作用,佛教文化交流將會對中蒙兩國間的關系產生一系列的促進作用。通過佛教文化開展人文交流和公共外交具有民間信眾基礎,會有明顯的社會文化效益。在經濟建設層面,還可以基于《中蒙戰略伙伴關系中長期發展綱要》中具體合作框架,打造中蒙跨境宗教旅游精品線路,這樣更能有效推動中國“一帶一路”建設和蒙古國“草原之路”規劃的務實對接。這樣,中蒙兩國間的宗教事務與世俗事務才能夠產生更加密切的良性互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