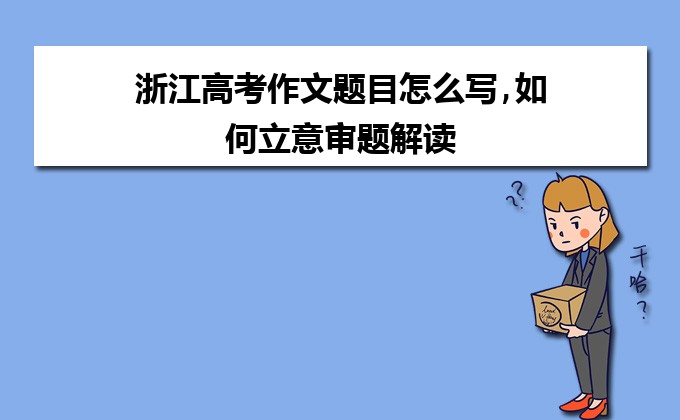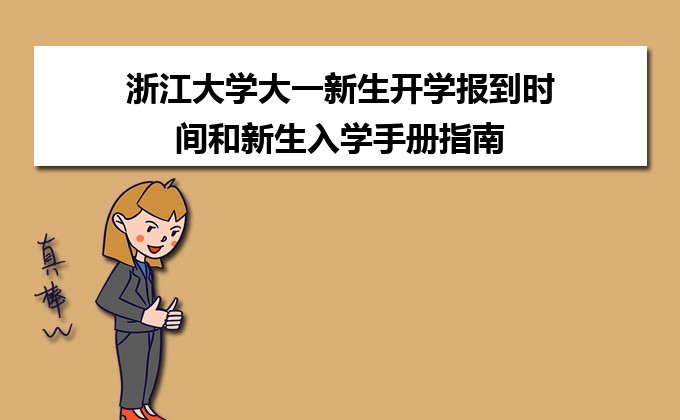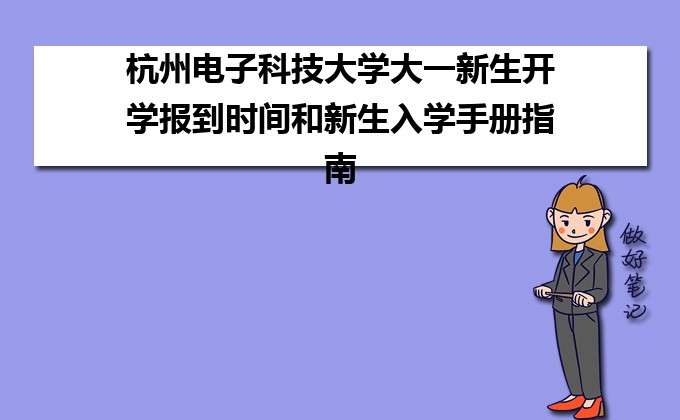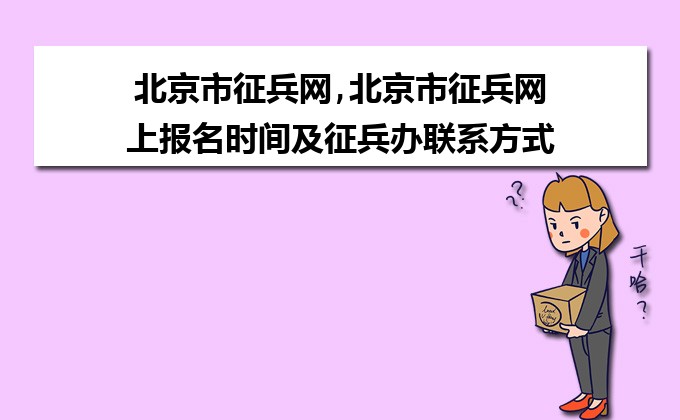浙江高考作文怎么寫如何立意,分析及點評
近日,網上公布了今年的浙江省高考滿分作文,全省14篇,其中兩篇出自金華一中的學生之手,他倆是已經在北京大學法學專業就讀的文科班學生雷琦,中國人民大學國際政治專業就讀的學生蘇暢。
滿分作文怎么來?據金華一中2015屆高三語文教研組長呂云清老師介紹,滿分作文起碼要過4關,先由兩名評卷老師“背靠背”打分,如果他們不約而同地都給了滿分,就要交給第三名閱卷老師,再通過閱卷組長的審閱,排除抄襲、套作等各種情況。只有這四輪環節中全部拿滿分,才能真正成為高考滿分作文。浙江省的考生每年有30來萬人,高考滿分作文一般篇數很少,每年通常只有幾篇或十幾篇,很少有幾十篇的時候。
在今年高考中,金華一中文科700分以上的有10人,排名在全省前100名的有6人,[MS1]排名前50名的有5人,雷琦排名全省第12名、楊思思全省第16名。還出現了語文高分群:130分以上有14人,高三(14)班語文平均分120分。
高考滿分作文作者雷琦,語文考了140分,是罕見的高分,雖然不能斷定她是語文學科的省狀元,但可以確定的是,她一定是少有的幾個語文高分考生之一。雷琦寫得一手漂亮文章,之前獲得過語文報杯省特等獎、博雅杯比賽的一等獎,她因此獲得復旦大學自主招生資格,在自主招生考試中,作文也是滿分,全國第一名,復旦大學因此給她提供了最大的優惠:只要高考上一本線就可錄取。
不過,在高考前的幾次模擬考中,雷琦的語文作文只有45分左右,這是作文的平均分水平。雷琦很傷心,哭著找呂老師問自己究竟哪里沒寫好。
她為什么寫不出高分作文?呂云清老師說,她是沒搞明白考場作文怎么寫,考場作文與平時的隨筆有所不同,它講究的是章法、規范,有自己的樣式。而這些平時文章寫得好的才子、才女,因為有大量的閱讀基礎,寫的文章一般很有思想,也很有個性,往往與考場作文的樣式有些不符合。語言上,有些學生往往過于含蓄,但高考閱卷老師只有很短的時間判定一篇文章,如果老師沒來得及讀懂其中蘊涵的意味,就很容易錯失一篇好文章。呂云清老師說,怎樣讓寫作高手在考試中拿高分?他給出了拿高分的絕招:不但要文章的開頭和結尾點題,而且要段段點題,點化主旨。因為她的語文功底好,語言有文采,完全不用擔心遣詞造句、組織材料、結構全文等問題。就在高考前的一個月,雷琦才學會這種考試作文的寫作方式,沒想到,就拿了個滿分。
高三(10)班的方涵藝,參加南京大學的自主招生考試,被一眼相中,給予她降分到一本線的優惠條件,全國得到該資格的全國只有4人。
文科實驗班學生季昊亮,在自主招生報名的時候,用文言文寫了一封自薦信寄給人民大學,那篇文章恢弘大氣、辭藻華美,據說考官們用了四五個小時來逐句解讀,對他的才華贊不絕口,還沒等到考試,就提前給予他降分30分錄取的優惠資格。
在金華一中,像這樣的例子還有不少。孩子們文采卓然,才華橫溢,近些年來,金華一中的語文成績特別耀眼。
附:2015浙江省高考滿分作文欣賞
我手寫我心
三(7)蘇暢(金華一中)
明代公安派作家有著這樣的為文之風:“為文必獨具一格,不拘性靈,非以自己的胸臆流出,不肯下筆。”在我看來,這便是對“言為心聲”的最好詮釋。
你心中汩汩然流淌著的是什么,你筆下流淌出的也應是什么。怪俠金圣嘆有二十四個“不亦快哉”流傳于世,那便是他的心中所想著的人間愉快。但現今社會或者說是古今社會上總有藝術家不能使其為人與作品相稱的現象,究其根源,原因大致分為兩種。
一類是作家在虛名浮利之中失去了自我,淪為了全為稻梁謀的“作家”。李紳因為寫《憫農》而聞名內外,卻不想他后來竟成了一個奢侈無度的豪紳,他的為人也就不能與詩中所云相稱。另一種情況便是難言了,雖有“物不得其平則鳴”之說,但在一定的社會壓力下,有時“鳴”卻是極為困難的。李賀詩中雄奇的想象,奇詭的詩風看似另類,卻恰恰包含了他懷才不遇之悲憤。至于晚唐李商穩,其眼中的蠟燭泣淚也是他的胸中之苦悶,只是無法直接訴諸筆端。
曹丕《典論?論文》中有言,“大丈夫見意于篇籍,寄身于翰墨,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句聲自附于后。”在科技發達言論自由的今天,我們應強調“我手寫我心”,而不是無病呻吟或是穿蠹經史,一個現代公民應能夠并且能夠恰當地發出自己的聲音,用文字指點江山。
現今社會已基本沒有“難言”的限制,我們要做的便是守住一顆本真的心,不沉浸于蝸居虛名,而忘記文字本身所具有的喚醒人類良知的作用。作家陳遠曾在訪談中這樣說道,美的本質是真,倘若過分追求美以致失了真,便背離了寫作的方向,先有真然后有美,我手倘若寫的不是我心,而是一些矯揉造作的故事,那么美就不會存在于這些文字之中。
先為真人,后為真文,此美之所源也。韓愈筆下的李愿使為一真人,他窮居而野外,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于是他成就了隱士的美名。我想,真存在于每個人心中,而且,這種真實的靈氣也會通過文字展現出來。
我手寫我心。長杯芳草,喜木美竹,皆可入心,皆可入文。不必拘泥于外在而含真,穿過重重花徑,自有云白山青。
輕嗅文骨的芬芳
雷綺(金華一中)
傅庚先生在《中國文字欣賞舉隅》中拋問:后生學者,文與心道契否?“有人筆底波瀾萬丈,心中槁木死灰;有人拊掌大樂,文飾不堪,徇名逐利;有人天生潔癖,抱守真,留戀理想國;有人拍案而起,剖心燭照,敢放一把野火,澤被寰宇,筆談間氣吐霓虹!
“性靈彰道著,文骨載風儀。”這是梁漱溟先生《究于決穎論》中對我輩殷殷的企盼,文品人品,誠有二律背反之意。我們這一代的寫手,又該如何認識此間命題,如何安放自身,達到兩者圓融之境界?
不可否認,作者格調趣味與作家人品背離并非罕見。艾布拉姆斯于〈鏡與燈???文學批評原論〉中將其斥為“解密過程”,作者、載器、讀者、時代四者循環返流,四元素也難以逃脫“橫態性欺瞞”。冷眼旁觀,〈被禁錮的苦惱〉中朱沃什?切瓦夫執借鷹隼雙目,銳意指出集權時代俄羅斯作家淪為“夜鶯群像”,文骨分崩離析,人格成為悲劇附庸;縱觀中國文脈史,沈括著《夢溪筆談》,可謂等身煌煌,但卻在政壇迷霧中墜落朽垮,鬻聲于物,為蘇軾的坎坷仕途復添艱險。究其根源,這些作者并非將心魂血肉潛入文章;傳入注意的是,他們將文字作為可恥的工具,即雅克?巴爾贊《從黎明到衰落》中指摘的“橫態木偶”。毫無敬畏,毫無熱忱,毫無神圣與崇高,他們就像敏銳而貪婪的漁夫,慢慢拉起漁網,渴望從虛空中找出某種寶物。文章為其操縱奴役,其本身復為功名利祿嘲弄把玩,果真是莫大的諷刺民侮辱。
我們這一代,又該如何保持文學的純潔性,達臻“真文學”的藝術之境?我以為一在讀者,讀者可謂是卡夫卡式的“判官”,得秉持著清醒與鎮定,不被妖艷可人的文辭灼作而眩暈,可以借鷹隼銳利之眼,剖開藝術的真境實例。北大有個傳統,叫“沉潛”,沉入藝術的源頭根蒂,潛進人生的幽微百態,從而抵達人品文品熔為一爐的高超境地。做到“沉潛”,便能撥開重煙迷障,直與作者對話。
二在寫手,即我們本身。就像《中國哲學史》中胡適先生所說:“文”道不是漂亮虛榮的外衣,而是本性的吶喊與沉思。這聲吶喊,理應震撼天地,就應發聵蒙昧之心,我們在屈瑞林大師《真摯與誠實》中聽見,我們在福柯《瘋癲與文明》的“失落天真”里聽見,《俄狄浦斯王中的勇士啊,不愿沉湮于鼾聲、風,真筋骨未鈍、腕血未冷,向世間問一問為此的意義,不正是我們的寫照?
父親曾笑談,年輕的夜晚,躺在床上渾身戰栗,想到什么半夜黑點起蠟燭,光著膀子抓起筆就寫,我從小便“雄心勃勃”想成為作家,每當獲得師長的肯定,外面的嘉獎,父親總要提醒我不能讓文骨背離了人的風儀,拿出季羨林研究人員吐火羅文的真摯,陳寅恪力挽史瀾的魄力,梁啟超冰鑒灼灼的溫度,感化他人,圓滿自身,所以說是“幾時借得沖霄浪,雖死望峰亦從容”。
行文至此,輕嗅文骨的芬芳,詩人的聲音也不必低吟:
爬學史乘扶叢殘,文章存軼堪顛沛。
拋棄詩興青云見,自誓夜闌熱腸心。
足跟踏破關山路,眼底空懸海月秋。
龍泉隱篋鋒未減,勢將重拳拋煙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