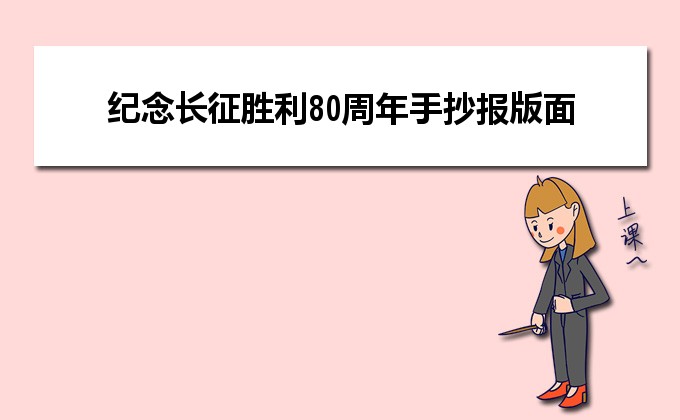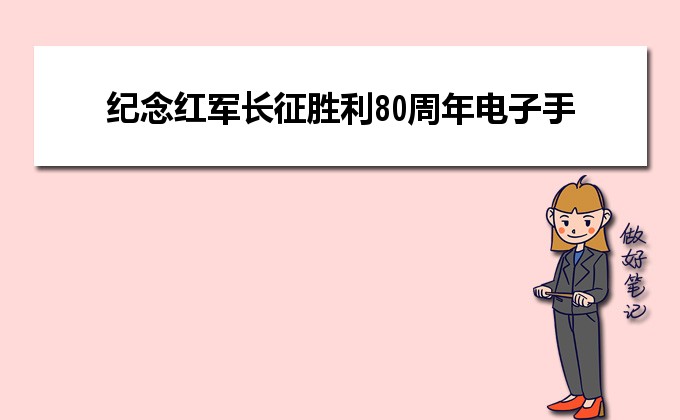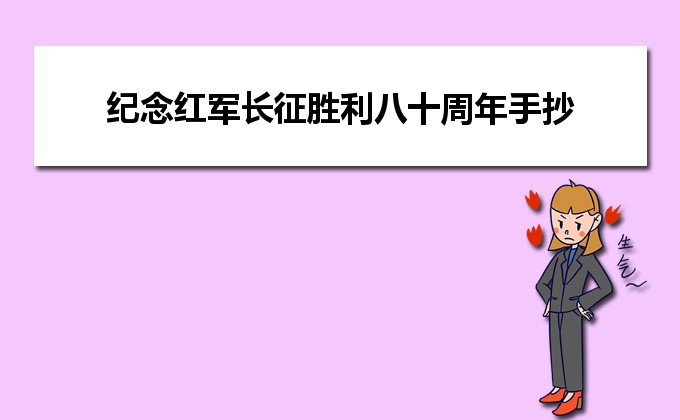長征是歷史記錄上的第一次,是震驚世界的偉大壯舉。中央紅軍在一年中,長驅2萬余里,縱橫11個省,實現了空前規模的戰略大轉移,終于使中國革命轉危為安,開辟了中國革命勝利前進的道路。下面是為大家搜集整理的2016紀念長征勝利80周年手抄報圖片,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而被迫進行長征,傳統的黨史歸因于王明、博古的臨時中央在政治和軍事指揮方面犯了左傾錯誤。自延安時期到今天,盡管細節有所變化,但這一解釋的基調卻一以貫之。國外學者的話語形式和立場不同,但基本上沿襲了這一說法。這種解釋的核心,把失敗的原因定位在軍事戰略戰術的錯誤和*的教條主義傾向。就中共而言,這種說法所隱含的邏輯是,左傾錯誤來自蘇聯和共產國際,只有中共的獨立自主,才能取得中國革命的勝利;只有毛澤東才代表了中共的自主力量,才能挽救中國革命。顯然,這種說法,實際上構成了延安整風以來中共黨史解釋學的核心部分,是毛澤東及其思想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合法性的主要來源。然而,近年的相關研究已經證實,中共黨內其實并不存在著一個以王明為首的左傾集團;所謂左傾錯誤的某些基本做法,在毛澤東主政江西蘇區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了;其中的肅反錯誤,所謂左傾*并不比毛澤東走得更遠[1]。事實上,這一時期紅軍之所以相繼從主要的根據地撤出,進行逃跑式的“戰略轉移”,標志著中國蘇維埃運動的失敗。這個失敗,實際上是中共這一時期革命與動員模式選擇的必然結果,而其政治和軍事策略的失誤,在正宗的中共黨史解釋學里,被過份夸大了。
一 革命動員與土地革命模式的選擇
中國共產黨人上山做“山大王”,本是城市暴動和武裝冒險失敗之后無奈的選擇。然而,中國當時前現代的經濟、交通與通訊狀況以及軍閥割據的形勢,給這種“農村道路”提供了空間。即便如此,在沒有“革命形勢”的情形下,要想動員農民參加革命,投入造反,依然是個難題,非有非常手段不能奏效。
在動員手段和形式的選擇上,進入農村的共產黨人,最初選擇的是“燒殺政策”,即把所到之處的富人殺光,所有的房屋燒光,先將農民這種小生產者變成赤貧,然后再驅使他們革命。在中共黨史上,這種政策記在瞿秋白的賬上,其實它帶有非常明顯的蘇俄內戰時期輕視農民的印記。這種做法迅速激起了農民對共產黨人的反抗,所以,很快就被廢置不用了。
以土地革命的方式進行革命動員,不僅具有歷史上的延續性(跟大革命時期的農民運動銜接),而且在“均田”的表達上,也有國民黨政府所無法全然否認的合理性(孫中山的“耕者有其田”)。但是,土地革命的實質,絕非共產黨和農民之間在土地上出現給予和支持的交換。首先,農村的危機,未必在于土地占有的不均衡;其次,共產黨給予土地,在農民看來,未必有合法性;其三,給予土地的好處,能否抵得上“造反”的危險,在農民看來肯定是個問題。也就是說,如果沒有其他的手段,即使分給了農民土地,農民也未必會跟著共產黨走。所以,所謂土地革命,在運作過程中,必然是“均貧富”的過程,或者說,對富人的剝奪過程,而這個過程,必然伴隨過度的暴力。平分土地,往往變成了一種由頭或借口。實際上,共產黨人首要的目標是要動員農民起來跟他們革命,而非借革命來解決農村的土地問題,所以,動員才是土地革命要解決的首要問題,而對于動員而言,均貧富式的剝奪和暴力的氣氛,是絕對必要的。
正因為如此,我們看到,在蘇區土地革命的政策上,基本上不存在左右之分。各個紅色根據地的土地革命,基本上都執行對地主(實際上是所有的富人)不給出路甚至肉體消滅的政策。在“分田地”的問題上,較早的井岡山土地法、興國土地法,根本就沒有提富人分地這回事,1930年的《土地法》提到,如果蘇維埃審查批準,“豪紳地主及反動派的家屬”,“得酌量分與田地”[2],但同一時期閩西特委關于土地問題的決議依然規定,反革命者及家屬不分田[3]。次年,這個土地法受到蘇區中央局的批判,1931年底成為蘇區正式法令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則明確規定,“被沒收的舊土地所有者,不得有任何分配土地的權限”;“富農在被沒收土地后,可以分得較壞的『勞動份地』”[4]。實際上,所謂的“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左傾政策,是蘇區一以貫之的政策,即使個別地區不那么過份,也會在隨后到來的糾正“右傾路線”的斗爭中被“糾正”。
對于能夠享有分配土地權利的農民,中共在具體做法上,也有文章可做,當時有兩種分配意見,一種是按勞動力分配,一種是按人口平均分配。前一種意見主要考慮如果不按勞動力分配,在蘇區就會造成“有力者無田耕,有田者無力耕”的現象,造成“經濟恐慌”。而后一種意見則認為平分對動員有利。毛澤東主張后者,他認為,經驗告訴我們,只有平分,才能“奪取整個群眾”,而“初起來的區域”尤其應該按人口平均分配[5]。贛西南特委書記劉士奇也認為,雖然按勞動力分地可以增加生產,但目前“爭取群眾”“發動斗爭是第一位”[6]。顯然,分配土地僅僅是動員的手段。因此,在中共控制下不長的幾年里,“土地分配了無數次”[7],地權頻繁變動,其意不在給農民土地,而是為了動員之便。每分一次土地,都會打倒新的富農,還會增加農民對紅軍和蘇維埃政權的依附感。
當然,僅僅分地達不到動員應有的深度,必須有暴力和暴力氣氛。所以,對富人的肉體消滅,尤其是現場的流血,是必要的。海陸豐蘇區剛一開辟,十幾天功夫,海豐一個縣就有豪紳和其他反革命份子1,686人被殺,沒有死的紛紛外逃。一時間,海豐、陸豐兩縣,逃到汕頭和香港的達萬人以上[8]。紅四軍南下,開辟新區,閩西地方黨組織暴動響應,“開宗明義的工作便是繳槍殺土豪燒契三種”,“土白暴動三四天內殺了四五十人,而(龍)巖永(定)兩縣革委成立后,日日都有幾十土豪反動份子被農民捆送到前來,致縣政府臨時監守所常有人滿之患。統計(龍)巖、永(定)三縣赤色區域中自斗爭后到現在所殺土豪總在四五百人以上。現在赤色鄉村中的土豪殺的殺,跑的跑,雖然不敢說完全肅清,然大部肅清是可以說的。”[9]海陸豐根據地有“七殺令”,所有富人,都不能幸免。湘贛蘇區土地革命,將“十六歲以上卅歲以下豪紳家屬的壯丁無論男女都殺掉了。”說是要把“有能力反革命的”預先除掉[11]。贛西南蘇區,土地革命的時候,“農村的豪紳地主,簡直沒有生存的地步,捉的捉,殺的殺,逃跑的逃跑”。
沒有被當場殺掉的富人家屬,如果沒有逃走的話,活命的可能也是沒有的。川陜根據地的文件《糧食問題回答》中,就有這樣的內容:
問:地主豪紳的家屬是否留點生活給他?
答:地主豪紳整窮人,不管窮人死活,現在蘇維埃只是要窮人個個有吃有穿,地主豪紳家屬集中起來在蘇維埃監視之下做工開荒都行,不留一寸土地一口糧食給他們。
不僅如此,殺人的時候,往往要造成某種血腥恐怖的氣氛,開大會公審,當眾處決。海陸豐的行刑大會,不僅喊口號,還吹著沖鋒號,行刑者揮舞著鋼刀,“一刀一個,排頭砍去,很爽利的頭顱滾地”。甚至還有婦女組織的“粉槍團”,在幾千人的大會上,用紅纓槍“刺進宣布了死刑的反革命份子的咽喉、胸膛,鮮血四濺。”[14]顯然,血腥可以喚起革命熱情,只要殺戒一開,參加的人就都跟反革命有了血海深仇。起初,“蘇維埃政府要撥給兩塊大洋賞給施刑的赤衛隊員,半個月后,不須要賞金,赤衛隊員要殺一兩個反革命份子雪恨。”[15]仇恨和仇殺就這樣被點燃,然后升級擴散。選擇了“立場”的農民,跟另一部分人誓不兩立,到了這般田地,動員的目的也就達到了。當然,很難估量跟著紅軍走的農民的真實想法。即使據中共自己人當時的考查,有的地方也有相當多的農民實際上是害怕紅軍,贛東北地區流行一句話:“莫惹紅軍,惹了遭瘟。”[16]
誠然,中共能夠在農村發動革命,前提是近代以來,農村社會與經濟的衰敗與戰亂和變革造成的鄉村秩序紊亂。然而,即使存在這樣的社會條件,想要在農村發動一場在一般農民看來屬于造反的農民革命,并非易事。對于那些真正的莊稼漢來說,分財主的土地糧食和財物,雖然有一定的誘惑力,但顧慮依然很大。所以,這里就用得著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里說的“革命先鋒”了,那些在鄉里“踏爛皮鞋的,挾爛傘子的,打閑的,穿絲褂子的,賭錢打牌四業不居的”流氓無產者,很快在革命中起了沖鋒陷陣的作用[17]。當時蘇區的共產黨人也承認,“在紅軍初到來時,一切情形不熟悉,最初起來的大部分是些富農流氓份子,真正的下層工農群眾最初不敢起來,所以在過去的政權機關完全是被富農流氓把持”[18]。其實,任何地方都不存在富農流氓這種“階級成分”,之所以這么說,一是要強調“階級觀點”,二則很可能是那些流氓無產者通過革命,變成了富農(浮財撈得比較多)。由于土地革命本身并非意在土地,流氓無產者的先鋒作用,使得運動在財產(主要是浮財)的剝奪和分配上的色彩更加濃厚。以至于動員起來的農民,參加革命的動機,往往更在意財產的掠奪和再分配,導致蘇區對外的“打土豪”一波接一波,內部反富農的斗爭一浪接一浪。每當紅軍攻城拔寨之際,總有大批的農民挑著空擔子,準備一旦城破,就進去發財[19]。
二 “打土豪”經濟及其局限
這種急功近利的動員模式,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產生了蘇區的“打土豪”經濟。由于土地革命的首要目的在于動員,甚至為了動員而犧牲經濟,而蘇區為了生存,養活軍隊和政府,又必須有一定的經濟來源。因此,一種畸形的經濟模式應運而生,這就是“打土豪”經濟,其表現形式主要有二:對內是均貧富,采取不斷革命的方式,削平蘇區內部的冒尖者以取得資金財物;對外則通過不斷擴張,或其他方式掠奪白區(國民黨統治區)的富裕者(包括商戶)。在整個蘇維埃革命時期,后一種形式是主導性的;前者的發展,往往受到后者的影響和刺激。井岡山根據地創始人之一的紅軍叛將龔楚,回憶說紅四軍之所以南下贛南閩西,是由于“井岡山的附近地區已民窮財盡”,要想維持下去,必須占領較大的城市,解決補給問題[20]。當時的湘贛邊區給*的報告里,說得更明白,井岡山地區的殘破,主要原因是紅軍的政策:
因為紅軍經濟的唯一來源,全靠打土豪,又因對土地革命政策的錯誤,連小資產階級富農小商也在被打倒之列,又以大破壞之后,沒有注意到建設問題,沒有注意到經濟恐慌的危機,以致造成鄉村全部的破產,日益的崩潰。
然而紅四軍南下,開辟了大片新區之后,打土豪的方式依舊,形成了方法上的路徑依賴,到紅軍和根據地發展到相當規模時依然如此。派駐中國的共產國際代表1930年在給執委會的報告里說到:
(紅軍)軍隊的糧食和服裝供給問題直到現在還都十分混亂。到目前為止這個問題在最好的部隊里基本上是通過向城市資產階級征收服裝料、縫制費和資金及征用地主豪紳和高利貸者財產的辦法來解決的。
報告人憂心忡忡地指出:
隨著紅軍數量的增加和在固定的地區建立根據地,這個問題就要求有新的解決辦法(顯然需要某種征稅方法),同時它將成為軍隊和蘇區農民相互關系中的一個越來越重要的問題。
顯然,只要紅軍的擴張勢頭尚好,在根據地內部發展正常的經濟模式來解決紅軍的補給問題,就不可能得到認真的對待。
不僅紅軍補給依賴打土豪,就是各級蘇維埃政府的經費,也要靠打土豪。1931年9月,歐陽欽關于江西蘇維埃的報告中,承認“各級政府的經費仍然是過去所謂打土豪來的。”[23]中共江西省委在1932年頭四個月的工作總結中指出,江西蘇區“財政的主要或者說唯一的來源是『打土豪』,而對于土地稅商業稅的征收,及發展蘇區的經濟政策是沒有的”。1932年紅軍攻下福建漳州,打土豪的戰果達到了頂點,幾乎所有店鋪,包括著名華僑資本家陳嘉庚的店鋪,其貨物都被無償征收。左右江根據地,為了打開交通線,利于通商,
紅七軍第三營營長雷祝平以私人關系,電邀南寧、那坡打商人黃祖武(黃恒棧的老閭,經營百貨及船航業)來百色商量,但他乘輪剛進入蘇區到達果化,即為紅七軍政治部下令第一營逮捕,認為他是一個大資本家,那坡打的黃恒棧即行沒收(據說有一個連長在黃恒棧拿了許多金條,發了洋財),還要罰款30,000元,用鴉片繳納,始得釋放。
在“打土豪”的視野里,紅軍原有對民族資本和小商人的特殊政策,已經化為烏有,這對后來根據地的貿易,產生非常惡劣的影響。
應該說,在1929到1931年紅軍發展較為順利的時期,由于大規模的軍閥混戰頻仍和國民黨政府對應失策,紅色區域經過土地革命的深度動員,迸發出了巨大的能量,對外擴張總的來說還比較順利。新開辟的紅區,特別是中小城市,基本上滿足了紅軍的補給需求。這種凱歌行進的擴張,也使得紅軍更加注重用擴張的方式,打土豪來解決自身的補給問題,輕視根據地內部的生產恢復和發展。在占據了相當大的區域(包括一些中等城市)之后,內部建設依然按照革命初期的動員模式慣性行進,不間斷地肅反、反富農路線、反右傾,內部的整肅和革命一個接著一個。這樣,原本就因地權動蕩和缺乏生產激勵的農村經濟,更加雪上加霜。農民為了避免冒尖,被人當富農來共產,普遍缺乏生產積極性,幾乎沒有人愿意多種地,只要自己家人夠吃就行。各個根據地,都出現了大量田地拋荒的現象,愈是老蘇區,拋荒田地愈多[27]。當時有的中共文件稱之為“農民怠工”。有的則認為產生這種現象是由于侵犯中農亂打土豪的錯誤,“以及分田分得次數太多,使群眾一般的走到安貧和不相信土地是否他自己的觀念”。
然而,到了1932年,國民黨政權逐步敉平了各地軍閥的反抗,穩定內部之后,紅軍的擴張勢頭就逐漸遭到遏制。蘇區面臨的圍剿的軍事壓力,逐年增大,與之相伴的政治與經濟封鎖也日趨嚴厲。在這種情形下,“打土豪”受到了極大的限制。但是,多年形成的行為慣性并未因此而消失,而且蘇區內部惡劣的經濟狀況,也不容紅軍很快改弦更張。各個部隊調整了打土豪的方式,采取派小部隊不定期進入白區的方式進行。龔楚這樣描述這種“游擊式打土豪”方式:
他們還不斷的深入到國府統治區內籌糧、籌款、就食;所以紅軍沒有作戰時,便開到“白區”去打游擊。這是紅軍官兵們最喜歡的工作。因為到“白區”去打游擊,就有土豪打。不僅是可以有充足的糧食,而且可以吃一頓豬牛肉下酒。他們打土豪的方式,是由政治部負責調查出某家是土豪之后,再由經理機關派出征發隊,由政治人員率領,協同紅軍部隊到土豪的家里,將其家所有盡數沒收。在屋內墻壁里及地下埋藏的金銀首飾,也要搜劫凈盡。要是土豪家中還有人留在家里,無論男女老少,一律拘回勒榨罰款,甚至槍斃處死。
不過,越界打土豪的方式很快變了味。土豪是有限的,而且是長腿的,財產可以隱藏、轉移,加上白區的防范愈來愈嚴,因此,打土豪愈發困難。土豪難打,但軍隊和政府的開支又必須解決,各地的地方部隊各行其是,各顯神通,于是大量的搶掠和綁票行動出現了,在中共自己的文件里,稱綁票為“越界吊羊”[30]。更有甚者,搶掠綁票的對象,并不一定限于有錢人,有的時候,甚至連窮人也被捉來罰款,“向貧農強借米物”,以致被白區人民呼為“游擊賊”。據曾志回憶,她的丈夫陶鑄,就曾綁過一個地主的孩子,得到贖金3,000多元。
這樣的“打土豪”,勢必會引起國民黨統治區老百姓的反感,甚至對紅軍和蘇區的敵視,這就是所謂的“赤白對立”(或者紅白對立)[33]。絕大多數資料在提到“赤白對立”的時候,往往要加上“嚴重的”或者“非常嚴重的”這樣的定語。傳統的中共黨史學解釋,往往把蘇區的經濟困難歸咎于國民黨的封鎖,其實,蘇區多在落后山區,像贛南閩西、鄂豫皖、湘鄂西這樣地方,山巒重迭,交通不暢,而且地域遼闊,切實實行封鎖無疑是很難的。恰是這種嚴重的“赤白對立”,才將蘇區真正封鎖起來。黃克誠在談到蘇區沒有鹽吃的問題時說過,國民黨的封鎖,固然是一個方面的重要原因,“而另一方面,由于我們實行過『左』的政策,把私商這條線也割斷了,等于自我封鎖起來,這樣就只好沒鹽吃。”毛澤東在抗戰時期總結這段歷史時,也曾對那時左的政策造成“赤白對立”,進行了反省,將之視為蘇維埃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之。
三 過度動員與蘇區的經濟危機
在這種嚴峻的情勢面前,蘇區*意識到了發展蘇區經濟的必要,各種稅收相繼開征,名目繁多的捐獻和攤派也浮出水面。除了土地稅、農業稅和商業稅之外,還有人口稅、養牛稅、屠宰稅、米谷稅、雞鴨稅、養豬稅、賣豬稅、園藝稅和飛機捐、慰勞捐、互濟會捐、反帝大同盟捐、節省糧食捐、新劇捐、歡迎捐等等,再加上攤派的公債。此時蘇區的人,顯然不能再說,“國民黨的稅,共產黨的會”這樣的謠諺了。同時,中共也開始注意發展蘇區的對外貿易,只是由于前一階段打土豪的結果,很少有商人敢來蘇區交易,蘇區的農產品和手工業品以及礦產品難以輸出,而外面的商品尤其是食鹽難以輸入;只有跟廣東軍閥,才能做點交易,也是杯水車薪。作為解困的一種方式,蘇區也開始花大力氣組織生產和糧食以及消費合作社,試圖用集體經濟來解困。自1933年8月以后,各種合作社的數量和參加人數都成倍增加,然而,這些合作社,由于存在“嚴重的缺點”,效果并不明顯,糧食合作社連“應有的調劑糧食的作用”都沒有起到[36]。為了解決財政困難,蘇區開始濫發紙幣,結果導致“蘇幣”的信用大跌,以至于蘇區不得不開展“擁護國幣運動”,提出“革命群眾用革命紙票”之類的口號,并對拒絕使用蘇幣的人加以嚴懲[37]。事實上,由于蘇區民眾的生產積極性一直不高,頻繁的分地以及斗爭,富人非死即逃,加上戰亂破壞,民間基本上沒有多少余財。常規手段顯然不足以滿足紅軍和蘇區政府的需要。
日趨嚴峻的“斗爭形勢”,往往更容易誘發人們的激進情緒,傾向采用更加嚴酷的階級斗爭形式,即過度動員的方式,高壓手段,解決目前的困難。“過度動員”的概念,是陳永發先生提出來的,但過度動員的產生,恰是打土豪經濟的內在邏輯。一方面,他們認為在嚴酷的戰爭壓力面前,只有不斷肅反和相應的“殘酷斗爭”,才可以保持蘇區軍民尤其是軍隊的士氣和凝聚力。同時,為滿足軍隊的需求,也要借助更加嚴厲的階級斗爭工具,采用政治斗爭和“運動”(查田,反富農),借強力從事征收。顯然,這兩方面,都有蘇俄在十月革命后內戰時期的“成功經驗”。不過,不管蘇俄經驗起了多大作用,現實刺激還是最重要的,愈是直接處在革命現場的*,表現就愈激進,這就是為什么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要遠比在莫斯科的王明更“左傾”的緣故。
早在1930年下半年,閩西就有“肅反籌款”的說法[38],1933年以后,更是變本加厲,所有反革命的家產,一律沒收,把肅反當成籌款的一種手段。不過,由于肅反對象不見得有錢,所以,更有聲勢的是反富農運動。此時的所謂富農,其實都是“新富農”,是土地革命之后有富余的農戶,按中共當時的說法,凡是從事小規模經營,飼養家畜,“分田時留肥短報,以及利用政權侵吞公款等”有了“多余存積”的人,都是富農,“過去一般中農及貧農中一部分,已經開始轉變為富農,同時有一部分中農及貧農,雖然目前還未成為富農,但他們卻含有或多或少的富農剝削,因此腦子里也有富農的幻想與企圖。”[39]所以,這些人都是運動的對象。1933年以來緊鑼密鼓進行的查田運動,實際上就是反富農運動,其核心內容,就是籌款。“查田是查階級,要把隱藏的地主富農查出來,不但查出來,而且要向地主罰款,向富農捐款,從經濟上去消滅地主,削弱富農,這是我們的主要政策,同時使蘇維埃財政得一很大幫助,因為目前急需籌得大批款子去接濟紅軍的費用。”具體方法則是,“地主應該捉起他家的人迫他交款,富農不必捉人,只嚴催交款,但頑固反抗的富農,也可以捉他起來以便催款。”
于是,在查田運動中,大批“地主”、“富農”被查了出來,瑞金黃柏區一地(轄十二個鄉),居然查出了“二百七十家以上的地主富農”,是過去三年中處置的地主富農數(122家)的一倍多[41]。據陳永發考證,毛澤東在查田運動中采取從寬定義的方式,以增加地主富農的比例,達到動員的目的。一旦目的達到,再給那些被劃錯者平反。即便如此,還是遭到中央的批評,被視為右傾[42]。
在這種高度緊張的氣氛下,甚至征糧征稅,發行公債也需要以動員的方式進行。1934年1月的全蘇代表大會明確提出,完成征糧征稅和發行公債的任務,必須真正依靠廣泛的群眾動員,必須學習興國永豐區,瑞金云集區,長汀紅坊區的動員方式,特別是興國長崗鄉,博生七里鄉的經驗,必須事先組織積極份子,在群眾中起領導作用,帶頭先交,必須徹底消滅過去對于推銷公債的命令攤派,及不做宣傳解釋,便進行推銷公債征收土地稅的官僚主義強迫命令方式,一切消極怠工,不去動員群眾,不相信群眾幫助戰爭的熱忱,只說:“群眾困難不能推銷”“非攤派無辦法”的機會主義與官僚主義的份子,必須受到無情的打擊。
這樣的無情打擊,落到了時任蘇區中央政府財政人民委員的鄧子恢頭上,其罪狀主要有兩條:
一、鄧子恢認為蘇維埃政府把種種稅金加到農民身上,使農民生活困苦,甚至比“革命”前更壞。二、在負責領導財政部工作期間,始終不發動群眾來做籌款工作,以為蘇區內的豪紳地主早已完全打倒,再沒有余款可籌了。
由于征稅和發行公債的困難是實實在在的,所以,在斗爭了官僚主義和機會主義之后,不動真格也征不上來,甚至強迫命令也不濟事,所以必須打擊反革命份子,“嚴查這些反革命份子,提到廣大群眾面前審判,把他提交法庭治罪”。顯然,要糧要錢,不流血是不可能的。
不過,即使依靠嚴厲的血腥手段、過度的動員方式,依然不能疏解蘇區的經濟困境。鄂豫皖蘇區在被放棄之前,1931年下半年,已經出現了糧荒,“外面不能輸入,內面儲蓄已罄”[46],只能“用互濟組織,割麥隊、割谷隊到白區奪取豪紳反對派的,沒收赤區地主富農的,節省(機關吃稀飯等,紅軍仍吃干飯),加緊生產(種瓜、豆、蕎麥)等辦法勉強過去。”
自1933年春天起,糧荒也襲擊了中央蘇區。機關工作人員被要求每天吃兩餐,只有十二兩,要省下四兩上交。后來,改吃稀飯,甚至米糠、苦菜和樹葉。列寧師范學校由于天天吃稀飯,被戲稱為“稀飯學校”。同時期蘇區中央政府的訓令中,也提到蘇區已經出現了將種子吃掉的現象,而且說“黃秋菜、筍子、苦齋、艾子、砂枯、同蒿、黃金(野山姜)苧麻葉等植物,都可采來充饑,并且無礙衛生。”要各級蘇維埃政府,組織群眾上山采摘,多種蔬菜,不能“放任不理,空口嘆氣”。為了救荒,蘇區中央政府還發布“開墾荒地荒田辦法”的命令,以免稅的優惠,鼓勵農民多種地;在這個訓令里,甚至連富農種荒田,也可以得到一年的免稅[50]。黃克誠在回憶中提到連中央紅軍的絕對主力紅一軍團,都沒有鹽吃,規定前線部隊勉強每人每天八分(不足一錢)鹽,而后方則沒鹽吃[51]。1932年底湘贛蘇區在給中央的報告里說,蘇區第八軍由于營養不良,腳氣病流行,全部人員不滿兩千,抵不上過去一個師,“還有一千上下的槍枝沒有人背。”[52]這樣的危機,一直到紅軍長征,都沒有得到絲毫的緩解。在長征前夕,蘇區中央政府的機關報《紅色中華》還登出號外,大字標題寫著:“紅軍等著二十四萬擔糧食吃!”到該年的7月9日為止,“糧食突擊(征糧的突擊──筆者注)還只完成一半任務”[53]。這一半,實際上已經是竭澤而漁了。
到了這個地步,蘇區的經濟危機,已經開始轉變成為政治危機了,主要體現在擴紅(即紅軍的招兵)上。進入1933年以后,蘇區的各種宣傳機器開始連篇累牘地鼓吹擴大紅軍,批評各種擴紅的不力,隨著第五次反圍剿戰爭進程,這種宣傳是愈演愈烈,表明了擴紅也愈來愈困難。戰況的不利,無疑加劇了擴紅的難度,一次長汀“擴大了五十七個新兵,但歡送到省蘇(省蘇維埃──筆者注)只剩了五個人,其中三個有病的,結果去前方的只二個。”[54]不僅擴紅難,紅軍中的逃兵也愈來愈多。在“『擴紅突擊月』──1933年5月的一個月中,紅一軍團(林彪部隊)逃兵就有203人;紅三軍團(彭德懷部隊)逃兵98人;紅五軍團逃兵200多人;紅獨立一團逃兵102人;而同年十一、十二兩個月中,開小差回家者,竟達二萬八千多人,僅瑞金一縣逃跑回家者達四千三百多人。”不得已,最后只好采取將地方部隊和赤衛隊整建制編入正軌紅軍的辦法,來補充兵源。蘇區老百姓對蘇維埃政權的信心也在整體滑落,在這一時期,有地方甚至出現了整鄉整村的農民逃往國民黨統治區的現象,以至于紅軍不得不嚴厲鎮壓[56]。方志敏領導的贛東北紅軍,作為紅軍長征先遣隊出發,結果一出蘇區,就被包圍打散,成千人連對方一個排的阻擊都沖不破,“指揮員動搖,不沉著指揮應戰,隊伍也就無秩序地亂跑”,基本上是全軍覆沒[57]。中央紅軍長征,在過第四道封鎖線時,損失過半,八萬人剩了三萬,其實也是逃亡的居多。據蔡孝干回憶,長征一開始,出了蘇區,紅軍就有大量逃兵,到第四道封鎖線的時候,“兵力已損失三分之一”。很明顯,此時紅軍的戰斗力和士氣,都已經今非昔比了。
四 余話
陳毅在1946年*的“五四指示”(關于土改)下達后,曾經說過:十年內戰時期的土地革命“走到平均分配一切土地,最后就發展到政治上、經濟上、肉體上消滅地主,以至消滅富農,并損害了中農,造成一系列的錯誤,走了陳獨秀的反面。同樣的絞殺了農民運動,在政治上造成黨和農民的嚴重隔離,造成了黨的孤立。”[59]作為動員工具的土地革命,最后走到動員的反面,“造成黨和農民的嚴重隔離”,無疑是中共*一種刻骨銘心的教訓,只是走到這一步,并非僅僅是所謂“左傾路線”之過。無疑,從蘇聯回來,受過系統馬列主義訓練的留蘇派,跟毛澤東等土生的共產黨人是有很大的不同。這個不同,在留蘇派看來,是布爾什維克化與否的區別,而在毛澤東看來,則是土包子和洋包子的分別,實際上則表現為土包子往往比較務實,尤其在戰爭策略的選擇上,更加靈活一些。這種分別和不同,并不意味著毛澤東就不是一個列寧主義者。從某種意義上講,毛比那些能背誦大段馬列原著的洋包子,對列寧主義更有悟性,至少作為革命家而言,他們其實心有戚戚焉。以“階級分析”來切割中國社會,高度的組織控制,用暴力和宣傳進行動員,革命手段的無限制,道義原則的工具化等等,在這些核心內容上,毛澤東跟列寧恰恰有著最大的相似性。所以,蘇維埃革命問題上,留蘇派和本土派本質上沒有太大的區別。
關鍵是,以動員為導向的土地革命,“打土豪”的經濟模式,以及靠嚴酷的黨內斗爭強化控制的肅反,這些蘇維埃革命的核心內容,毛澤東和留蘇派并無分歧。蘇區動員型的土地革命,實際上是毛澤東開創的,至于打土豪經濟,毛更是始作俑者。還在1930年,赤白對立的現象就已出現,只是到了紅軍擴張完全停滯之后,其惡果才充分顯示出來。事實上,只要打土豪經濟模式的存在,紅軍又不可能保持持續的擴張能力,那么,蘇區的經濟危機是遲早的事情。當然,至于以階級斗爭的恐怖手段來處理黨內外的一切事務,本是毛澤東的看家本事,只是毛比較中國化,講究有張有弛,因此效果更佳。至于軍事戰略戰術問題,應該說,毛澤東是要比李德為首的三人團高明一些,但是面對國民黨的政治軍事一體化的圍剿,堡壘戰術的堅定推行,毛澤東未必能有更好的辦法。
顯然,中共的留蘇派和本土派,在權力上存在紛爭,這種權力之爭,反映了蘇聯和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掌控需求。但這個爭奪,并不能改變蘇維埃革命失敗的命運。最根本的問題,在于蘇維埃革命的基本政治經濟模式的選擇,這種模式有速效,卻難以持久。中央紅軍是戰敗了,不得不退出根據地,而川陜蘇區的紅四方面軍,仗其實打贏了,但依然要放棄根據地。川陜蘇區的*張國燾后來回憶說,紅四方面軍之所以退出蘇區,原因之一就是:
川北蘇區經過戰爭的蹂躪,糧食及其他必需品均感不足,到了明年青黃不接的時候,可能發生饑荒,如果紅軍死守在這里,不僅不能為人民解決糧食問題,恐將與民爭食。
張國燾有沒有如此人道,慮及人民生死,姑且不論,但蘇區的經濟困難乃至危機導致根據地保不住,卻是不爭的事實。
動員式的土地革命,在動員農民造反方面的確成效顯著。這使得中國共產革命的農民戰爭威力巨大,歷代農民造反不能望其項背。然而,只有在動員效應的有效期內推倒國民黨政府,蘇維埃革命才能成功;否則,就會被自己催生出來的掠奪式政治經濟模式所吞噬。紅軍之所以長征,關鍵就在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