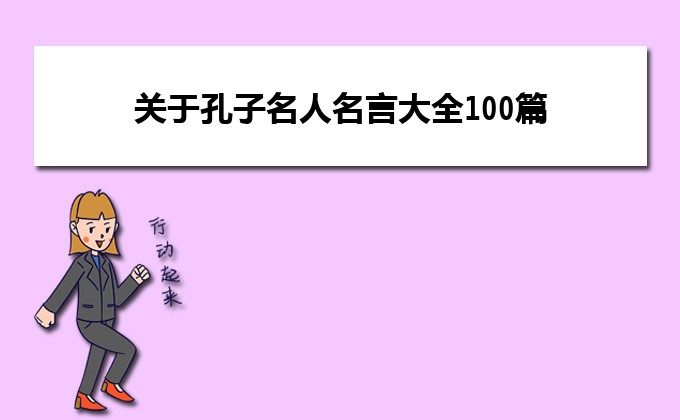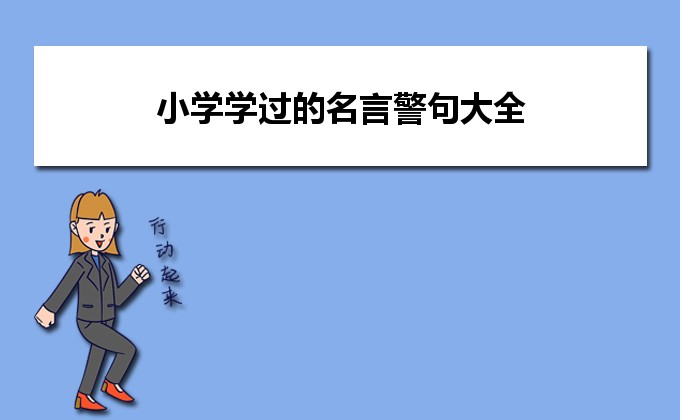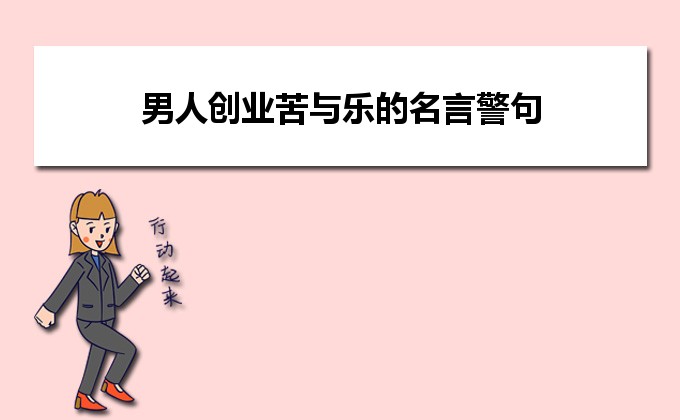王朔
整個十八世紀,猶如先前的一切時代,一個國王有沒有性功能,一個王后多子還是不育,這是被看作公開而并非隱秘的事,被看作國家大事,合歡床實與“王統”攸關,國祚所系。顯而易見,它同洗禮盤和棺材一樣,是人生的一個部分。
茨威格
一個國家居然會眼看著挨餓受凍的女人為了偷過兩角六分錢的咸肉或是破衣服而被處絞刑,孩子們被迫離開他們的母親,男人們被迫離開他們的家屬,他們只是為了類似的小小過失,就被流放到天涯海角,服長斯的徒刑——我們不得不想念對于這樣一個國家,“文明”這兩個字是不大適用的。
馬克吐溫
青年人滿身都是精力,正如春天的河水那樣豐富。
拜倫
在人的一生中,再也沒有像青年時期那樣強烈地渴望被理解的時期了。沒有任何人會像青年那樣沉陷于孤獨之中,渴望被人接近與理解;沒有任何人會像青年那樣站在遙遠的地方呼喚。
他發現,并非處處青山皆宜人,至少對一個青春已逝,走遠的時日將盡的人生說是如此。他越來越多地考慮怎樣為自己安排一個滿意的晚年。
海塞
她那玫瑰色的明凈的臉蛋,她那像是準備接吻的嬌嫩的雙唇,她那像海水一樣淡青的藍眼睛,她那像雪花石膏一樣雪白的額頭,她那彎彎曲曲閃站琥珀和哥林多青銅的光輝的一頭豐盛的黑發,還有她那柔軟的脖子,她那像“神”似的削肩膀,整個身姿既柔韌纖細又帶有五月春光和新開的花朵的青春朝氣……
《史記》
“被愛的箭射過的人,才能領會愛得力量是多么偉大的。”父親對我所采用的方式,正是用愛得箭射入我的心坎,使我體會到“愛的力量是多么偉大”。我下定決心,一定要堂堂正正地做人,光明磊落地活下去。
甘地
幾種省錢的簡單辦法:在你激于熱情、想要給一個慈善事業捐款的時候,你為了省下一半的錢,就不妨等一等,默數到四十。要想省下四分之三,就默數到六十。要想完全省下這筆錢,那就默數到六十五好了。
馬克吐溫
我們自己用的得意的詞匯,其實絕非來自我們自己。屬于我們自己的無非只是依照我們的脾氣性格環境教育與社會關系而做的些修改而已。只是這么點修改,使之區別于別人的表達方式,打下了我們特有風格的烙印,暫時算作是我們自己的東西。別的統統都是些陳年舊貨,是幾千年幾百年以來世世代代的人說過的陳詞濫調而已。
馬克吐溫
許多年輕人通過一個笨拙的——粗制濫造的謊言使自己受到了永久的傷害,這是不完善的教育所造成的輕率行為。有些權威人士主張年輕人根本不應說謊。當然,這話說得有點不必要地過頭;然而,盡管我不會走得那么遠,我卻主張——而且我認為我是對的——年輕人必須克制自己,不去使用這項異乎尋常的技藝。
馬克吐溫
孩子們被送進了學校,至少在當時,那總算是一個學校吧。柔弱的幼年一代每天在這里專心致志地苦干上十個鐘頭,從書本里學些他們所不懂的毫無用處的東西,依靠死記硬背,像鸚鵡學舌似的;因此受完了教育的成績只有兩點,一是永遠的頭疼,二是念書的本領——念起來流利得很,既不要停下來拼字,也不要換氣。
馬克吐溫
受教育懂得焚毀遺囑,做一個體面的人,為人所愛,受人敬重,而不是去做一個屢犯的偷表賊,受到法律對五種情狀的加重處罰,解赴格雷伏刑場處死,受人憎恨和名譽掃地。
巴爾扎克
人的內心里有一種根深蒂固的需要——總想感到自己是發現者、研究者、探尋者。在兒童的精神世界中,這種需求特別強烈。但如果不向這種需求提供養料,即不積極接觸事實和現象,缺乏認識的樂趣,這種需求就會逐漸消失,求知興趣也與之一道熄滅。
蘇霍姆林斯基
正因為無人不曉這陰沉的力量和它們危險的戲舉,我們才對沉默懷有深深的懼意。迫不得已時,我們忍受孤立的、自身的沉默,幾個人的、人數倍增的、尤其是一群人的沉默卻是超自然的負擔,最強的心靈都畏懼無以解釋分量。我們消耗大部分生命來尋找沉默統治不到的地盤。一旦兩三人相遇,他們只想驅逐看不見的敵人,要知道,多少平凡的友誼不是建筑在對沉默的仇恨之上?假如人們白費了努力,沉默仍成功地潛入聚集者之中,他們便會不要地從事物未知的莊重一面扭轉腦袋,然后馬上走開,將位置留給生人,從此便互相回避,惟恐百年之搏斗再次落空,惟恐有人偷偷向敵手敞開大門……
M·梅特林克
一個人上床的時候能夠對自己說:我沒有對別人的作品下斷語,沒有叫誰相信,沒有把自己的聰明才智當作刀子一般在清白無辜的人心中亂攪;沒有說什么刻薄話破壞別人的幸福,便是對癡呆混沌的人也不干擾他的快樂,沒有向真有才氣的人無理取鬧;不屑用俏皮話去博取輕易的成功;總之從來不曾違背我的信念……能夠對自己這么說不是極大的安慰嗎?
巴爾扎克
一個研究人員可以居陋巷,吃粗飯,穿破衣,可以得不到社會的承認。但是只要他有時間,他就可以堅持致力于科學研究。一旦剝奪了他的自由時間,他就完全毀了,再不能為知識作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