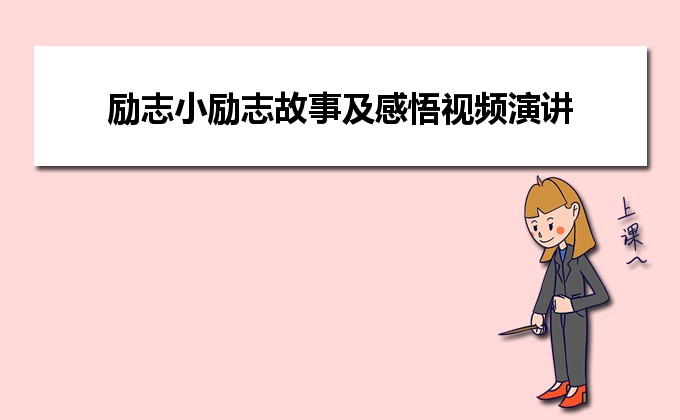“我有抑郁癥,所以就去死一死,沒什么重要原因,大家不必在意我的離開。拜拜啦。”今年的3月18日,是南京女大學生“走飯”發出微博遺言、在宿舍自縊的一周年。當張大奎在宿舍看到紀念她的微博時,他抬起并不靈活的雙手,敲下了四個字:“努力活著。”
這個從不到兩歲起被診斷為腦癱的青年,曾經也是離絕望最近的人,如今,他是計算機博士。
咱可不能穿新鞋,走老路
咖啡色的條紋襯衫,深藍牛仔褲,張大奎身體略有些傾斜地打開了門。
單間宿舍里,淺藍小花的被套、藍綠相間的床單都鋪得很平整。張大奎笑著說:“我奶奶給我講,你要把被子疊好,別人來看你的時候就會說:‘哎呀這小孩走路走不好,被子疊得還挺好。’”
1981年,張大奎出生在河南焦作的一個農民家庭。一次高燒,鄉下有限的治療條件導致了嚴重的后遺癥。父母把他抱到北京來求醫,卻得到了一個令人心碎的回答:“核黃疸后遺癥”,俗稱小腦癱瘓。
到6歲時,他還只會在地上爬,根本無法獨自站立。“這種病的主要表現是運動平衡、肌肉協調等功能有較大障礙。醫生告訴我爸媽,在醫學上沒有好的治療方案,唯一的方法是自己鍛煉,恢復部分身體機能,達到自理。”
沒有任何康復訓練機構,也不知道去哪里求助,但張家沒有放棄。
一開始,張大奎的爸媽在兩棵大樹間綁上了兩根竹竿。從烈日炎炎到漫天飄雪,年幼的張大奎雙臂架著竹竿挪來挪去,有時候哭著還繼續“走”。幾年后,雙臂磨厚了,他終于可以用雙臂“走”了。
但一個年輕人的天地,不可能永遠在兩棵樹之間。突然有一天,竹竿被換成了粗繩子,“竹竿是硬的,可以完全依靠;但繩子就不一樣了”。他很不適應,經常是走到一半就雙膝跪倒,“膝蓋不知道磕破了多少次”。
在張大奎摔倒的時候,爸媽很少伸手扶。“自己想辦法站起來”是他們的口頭禪。終于有一天,再摔跪在地上的時候,孩子沒有感到膝蓋疼,還馬上爬了起來。
到了9歲,張大奎創造了第一個奇跡:他能拄著拐杖走路了。
“說實話,當時我很恨父母對我的‘狠心’,但現在我非常感激父母當年的良苦用心,也特別體諒為人父母內心的掙扎。更慶幸的是,父母沒有放棄我的教育。”
從小學開始,這個孩子上課時不敢多喝水,怕上廁所的時候麻煩別人;在別的孩子追跑的時候,他只能孤獨地坐在座位上。“我不聰明,身體也不方便,很少出去活動或玩耍,這也讓我有了更多的空閑時間,那我就多花些時間學習”。
他能穿得起的只有十幾塊錢的軍用膠鞋。“腳在地上拖來拖去,所以每個月基本上要磨壞兩雙膠鞋。”
父親每次為他穿上新鞋子的時候,都會說一句:“奎,咱可不能穿新鞋,走老路。”“當年我并不理解這句話的含義,但若干年后,每當我有了新鞋時,我都會學著父親的口氣對自己說:‘咱可不能穿新鞋,走老路!’”
“沒有你們想象中那么困難”
“現在很多人看問題都很喜歡‘一刀切’,認為我很厲害,但我就是做自己能做的和該做的,一步一步走過來的,沒有你們想象中的那么困難。”白色的書桌上,攤開的是張大奎正在學習的英文課本,旁邊放著幾只專門用來練字的熒光筆。他寫的字很大,有專門練字的本子。“如果字太小,我掌握不了那框架,就寫歪了。”
講話時的張大奎還會加上手勢,語速一快就會有點口齒不清,不一會兒額頭上就出了薄薄一層汗。小毛巾就捏在手里,時不時地需要擦一下。“這么多年來,雖然心理和身體方面成熟了很多,也參加了無數的考試,但每次考試都是不小的挑戰。畢竟我要付出常人數倍的努力,還不一定得到一樣的成績。”
2002年,張大奎頂著極大的壓力參加了高考。“當時頭上的汗不斷落在試卷上,大部分試卷都被汗水浸透了。一場考試下來,兩條帶進去的干毛巾都像剛從水里撈出來一樣。我寫字也沒辦法快起來,字體會因為手臂顫抖很潦草。汗跡墨跡混在一起,卷面很不清楚。”
他選擇了當地一所民辦大專院校——黃河科技學院。“當年我參加高考的時候,絕大多數公辦大學都不愿意接受殘疾人,我的選擇余地很小。現在想來,很感激母校愿意接收我。”
大專快畢業的時候,他面臨了一次至關重要的選擇:是繼續讀書,還是就此結束?
“我當時看不到繼續讀書的希望。”張大奎回憶說,“因為不少身體健全的名校畢業生都找不到工作,更何況我的身體條件還是這樣?但父母知道我的想法后,既引導我,又逼迫我,讓我繼續讀書。為了不讓他們失望,我在專升本考試的前半年,都把自己關在宿舍里沒日沒夜地復習,連一日三餐都請同學從食堂帶回來。”
2006年,他考入河南理工大學計算機學院,并在那里讀完了研究生。“河南理工大學是改變我一生命運的地方。他們能夠接受一個殘疾人入學。考博時,河南理工大學還把輔導員辦公室讓給了我,因為我很難去搶占座位。”
,張大奎決定考博。“但理想和現實是有差距的,尤其像我這種情況。”
他給相關領域的博導們發了不少郵件,但是大部分教授在得知大奎的身體狀況后,都選擇了沉默或是拒絕。最嚴重的時候,他整夜整夜地失眠,也曾想過要放棄。但他曾對自己說過:“絕望也是種醒悟和升華。”
終于,他收到了唯一一封回信,它來自北京理工大學計算機學院樊孝忠教授:“你可以考我的博士,但是我不會給你任何特殊的優待,不會透露任何關于考試的信息,能不能考上,完全要靠你自己。”
這對絕望中的張大奎來說,是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
那一年冬天,他坐在輪椅上的身影,震驚了整個筆試考場。博士生面試那天,樊孝忠教授第一次見到張大奎。他在樓道里滑倒了,等大家發現的時候,他已經在努力地爬起來。“很自強,看起來似乎已經是習慣。自己能做的,即使朋友能幫,他也要自己盡力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