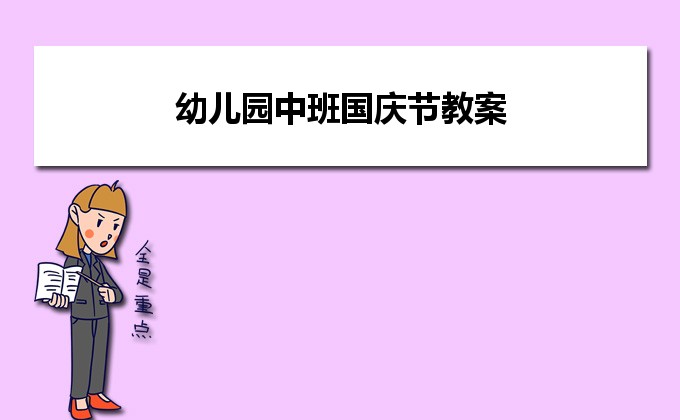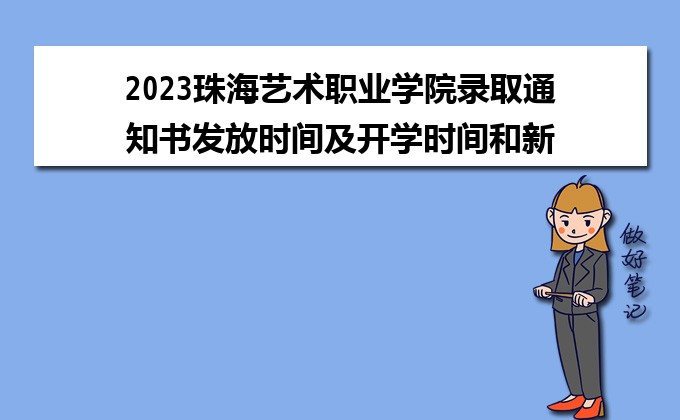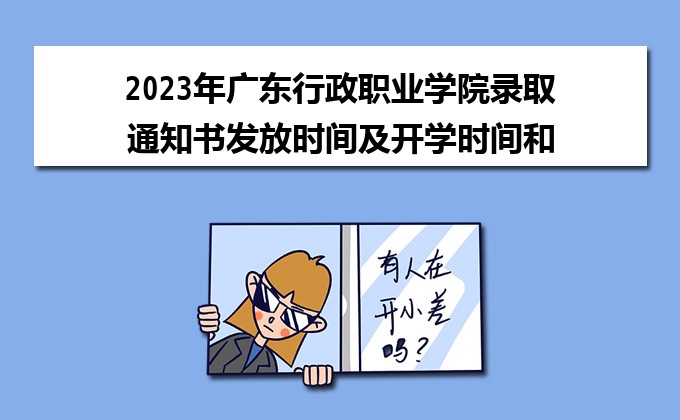8月23日,一場歷史學家的盛會將于中國的泉城濟南舉行。85個國家和地區、2615名中外歷史學者,使得這場當今范圍最廣、影響最大、素有“史學奧林匹克”之譽的盛會——第22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注定載入史冊,而首次在非歐美國家舉辦更賦予它與眾不同的意蘊與使命。
其實早在一個世紀之前,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創辦伊始,中國學者就從遙遠的東方投來關注的凝望,但“顧吾國竟無一人往焉”。從無緣參與的喟嘆到胡適孤身一人代表中國參會,從派代表團定期參會到作為東道主主辦盛會,歲月的年輪銘記了一代代學人為之魂牽夢繞、傾力拼搏的印記,也見證了中國史學話語走向世界的征程。
“唯學不如人,斯乃大恥”
1905年,著名報人和教育家黃節在《黃史》“總序”中提及1908年將在德國召開“柏林史學大會”,留下了中國學人關于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最早記載。
1923年3月,第五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召開前夕,一篇專門介紹大會及其歷史的文章引發了人們的好奇與關注。此時此刻的中國,正處于內憂外患、戰火連天的亂局之中,作者只能望洋興嘆:“各國學者必將聯袂偕來,討論學術,互顯國史……返觀我國,學術消沈,歷史學者至今猶無團體之組織,恐屆時終不能有代表出席,以各國績學之士相見也。”
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典籍豐富的文明古國,又是一個具有治史和修史傳統的國度,自古以來史家輩出,史著如林。然而近代以來,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的現實使得當時一批碩學鴻儒無用武之地,痛感報國無門。正如當時還是一名青年學生的史學家向達所言:“此次大會,自以歐美諸國為其主干,而我鄰邦日本亦有代表,參與其間……顧吾國竟無一人往焉!竊嘗謂一國萬事零隊,都不足悲,唯學不如人,斯乃大恥。”
“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也正是從這一時期開始,“中國為歷史悠久、史學發達之國家,自有加入之必要”成為中國歷史學人的共識,參加國際歷史科學大會活動、加入國際歷史學會成為前輩史家的奮斗目標。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史學會會長張海鵬對這段往事銘記在心。
但是,中國邁向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步履卻異常艱難。1938年8月28日,第八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在瑞士蘇黎世召開,45個國家約900名史學家到會。也正是在這次大會上,中國面孔第一次出現在國際同行面前。當時正在美國的胡適孤身一人代表中國參會,并作了發言。
“中國第一次參會,正值日本悍然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因此這一舉動除了加強國際學術交流外,更帶有學術救國的深沉的歷史責任與擔當。”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中國史學會秘書長王建朗指出,正如會前傅斯年所強調的:“此會系國聯所主持,是一鄭重國際學術會議,未可輕視。且其中包括近代外交史、遠東史,此皆日本人指鹿為馬、混淆視聽之處,吾國不可略也。”也正因為如此,胡適對于此行無比堅定:“Zurich(蘇黎世),我必須一去!”
“胡適之行是解放前中國學者唯一的參會行動。此后雖然新中國成立不久便正式組建了中國史學會,大家對大會給予極大關注,對會議情況進行了不少報道,但受限于國內外環境,此后仍一再與國際歷史大會失之交臂。”中國史學會副會長、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徐藍對此感慨不已。
改革開放帶來了學術成長的春天,也打開了中外學術交流的大門。1980年8月10日,當中國代表團作為觀察員出席羅馬尼亞布加勒斯特第15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時,“全場與會者起立鼓掌,整個會場響起了‘中國!中國!’的歡呼聲,情景十分感人!”長期關注這一問題的《中國歷史評論》主編、山東大學第22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專家咨詢組組長王育濟動情地告訴記者。
此后的一切便順理成章了:1982年9月,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在巴黎舉行執行局會議,正式接納我國史學家組織為國際史學會新成員;1985年8月25日至9月1日,以劉大年為團長的中國代表團一行20人以正式身份參加了斯圖加特第16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從此,每屆大會中國都組團參加,中國史學家的身影活躍于“史學奧林匹克”舞臺。
世紀之交,伴隨國家發展文化軟實力和文化走出去戰略,爭取在中國辦一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成為我們新的追求。張海鵬告訴記者:“我們準備了很長時間,做出了很多努力,也經歷了申請失敗的挫折。直到2010年8月在阿姆斯特丹召開的第21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上,經大會陳述、執行委員會投票等程序,我們的申辦最終獲得成功!”回想起其間的漫長過程和當時的情景,親歷投票的張海鵬依然難掩激動。
“機遇和榮譽體現進步與實力”
學術是一個時代的寫照。中國與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結緣實際上是與改革開放尤其是新時期以來中國的崛起、國力的提升及學術話語權的成長相伴隨的。王建朗認為,中國史學會申辦成功的背景首先是中國經濟發展取得重大成就。2010年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際地位和國際話語權空前提高。“機遇和榮譽體現進步與實力,也充分表明國際歷史學界對中國的重視和信任。”
文化軟實力和學術話語權從來都是和國家的政治、經濟地位相匹配的。武漢大學中國邊界與海洋研究院院長胡德坤表示:“歷史科學大會在中國的召開,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以往的會議多在發達國家舉行,此次在中國舉行,帶有某種象征意義,是中國崛起的表現、中國魅力的展現,同時也是中國歷史學科發展和中國史學會影響力擴大的結果。”
改革開放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歷史學研究不斷開拓進取,在理論、范式、研究手段和學科體系等方面呈現出生機勃勃、百花齊放的嶄新面貌:斷代史與專門史研究不斷深入;邊緣學科、交叉學科孕育出新;區域社會史、新文化史以及生態史、心理史等不斷拓寬史學研究領域。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卜憲群看來,這種發展和進步表現在史學研究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國家清史編纂工程、徽州文書的整理與研究、晚清與民國史料的整理與研究、《中華大典》的編纂等大型資料整理和專題研究項目取得令人矚目的成績。
清史編纂工程啟動于2002年,計劃用十余年時間,組織1000多位清史專家,創造性地繼承修史傳統,開展全面的清史研究,最終推出100卷約3000萬字的大清史。目前已整理出版一大批《文獻叢刊》《檔案叢刊》《研究叢刊》《圖錄叢刊》成果,在初稿全部完成基礎上開展統稿工作。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被稱為是一項承載著“中國考古學百年夢”的工程,這是國內迄今規模最大的綜合性多學科參與研究人文科學重大問題的國家工程。歷經十余年的探索與努力,工程各課題組對黃河、長江和西遼河流域20多處都邑性遺址和中心性遺址進行了考古調查、發掘與研究,復原了不同時期先民的生活情景,為最終揭開中華文明起源的神秘面紗打下堅實的基礎。
20世紀初,大量珍貴敦煌文物損失或流失國外,乃至有“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之說。這一狀況深深刺痛了中國學人的心,振興敦煌學成為他們的夙愿。改革開放特別是近年以來,我國的敦煌學研究取得重大進展,《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敦煌大字典》《敦煌學研究叢書》等一系列重大成果引起國際學界的矚目,使敦煌學回歸故里,并邁著自信的腳步款款走向世界。
2011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通過了新的學科目錄,世界史成為一級學科,開啟了學科發展的新階段。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錢乘旦介紹,世界史學科近年來表現出欣欣向榮的局面,獨立思考而非“拾人牙慧”的研究成果增多,環境史、全球史等研究領域擴展,高校人才培養規模擴大,國際學術交流活躍。尤其是非洲研究中心、東南亞研究中心、印度洋地區研究中心、拉丁美洲研究中心等區域研究中心相繼成立,并充分發揮世界史學科關照現實的智庫功能,服務于國家和社會的發展大局。
“本屆大會上,中國歷史學者將參加所有場次的討論,不只是全球性歷史問題,還包括某些區域歷史。這說明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歷史學研究范圍的廣泛性,也說明我們達到了可以和世界同行并肩對話的水平。”山東大學歷史學院院長方輝是此次會議籌備的主力,他十分自信地表示。
除了專業研究的繁榮發展,史學研究也逐漸走出書齋,與時代發展和日常生活的關系日益緊密。中央文史館館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史學會副會長陳祖武指出,近年來的讀史熱、國學熱顯示歷史開始重回人們的視野。提出“歷史是最好的老師”“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等重要論述體現了黨和國家對歷史科學的重視,必將使學習歷史、研究歷史、運用歷史成為越來越多人的共識,而這些無疑也促進了史學的進一步繁榮發展。
走出“西方中心論”,建構中國史學話語體系
“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為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交流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平臺,同時也是一個文化展示的大舞臺,可以展示我們的文化魅力、吸引力、影響力。”對于這屆體現東方特色和全球視野的大會,山東大學校長張榮充滿期待。
據組委會統計,注冊報名的中外歷史學家有2615名,注冊參會的國家和地區達到85個,突破了歷屆大會參會國家數量的最高紀錄。“從最直觀的層面講,這么多國家的參與正體現了大會所倡導的全世界史學家廣泛參與的國際主義理念,使1913年第4屆大會提出的‘全世界史學家聯合起來’的口號,伴隨著大會第一次在亞洲、在中國舉辦,伴隨著參會國家的突破性增長而獲得更加完美的意義。”王育濟的話語中滿是自豪。
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許多議題往往體現了國際學術熱點和前沿,帶給中國學者很多啟發。著名法國史專家張芝聯先生生前一直關注并參加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年鑒學派和布羅代爾等,就是他“請進來”的。參加過第19屆大會的錢乘旦撰寫的與大會主題相關的文章《探尋“全球史”的理念》,是國內第一篇全面介紹全球史的文章。著名西方史學理論專家、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張廣智也指出:“中國史學之進步,既需要內力,也需要借助外力,而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就是一種有效的外力。”
“近100年來,無論是蔡元培、傅斯年、胡適,還是胡喬木、劉大年、季羨林,他們在推動中國參與大會時,都曾反復強調過‘預世界文化之流’,即向國際學術界學習,豐富和發展中國的歷史科學。”山東大學教授、《文史哲》主編王學典強調,“中國史學家要想在國際社會有話語權,必須要關心和理解別人的話題。只有了解世界,才能進而為世界提供有價值的‘中國故事’和‘中國經驗’,才能具有真正的國際話語權。”
不僅如此,此次大會還將在幫助西方學者了解中國歷史學,推動中國歷史學、中國歷史學者走向世界等方面起到十分積極的作用,“必將會載入中國歷史以及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史冊。”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陶文釗興奮地說。
陶文釗還有另外一重身份: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執行局委員。據他介紹,每屆歷史科學大會的議題都非常廣泛,既要照顧到方方面面,又要有重點,起到導向作用。這次中國史學會充分發揮“主場優勢”,在議題設置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特別是大會四大主題之一的“全球視野下的中國”充分反映了各國歷史學家對中國歷史的興趣和研究已經提升到一個新的水平;在60多場分組會議中由中國學者主持(或共同主持)的達16場;以前中國史學會組團參會,一般只有20人左右,此次參會的中國學者則達到1709人,這些都是以往所不可想象的。也正因為如此,國際歷史學會秘書長羅伯特·弗蘭克稱贊:“第22屆大會將展示歷史學家們在擺脫歐洲中心主義或稱西方中心主義的研究框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
近年來,國際史學界有越來越多的學者正試圖擺脫西方中心論的窠臼,以全球史、跨國史等不同的研究范式分析和闡釋世界歷史。參加此次大會的芝加哥大學歷史系教授、“加州學派”代表人物彭慕蘭,曾在《大分流》一書中,以中國與歐洲雙向比較的視角,提出了許多創新性見解。中國史學工作者也意識到這一問題并付諸實踐。錢乘旦說道:“我們現在已經有些研究型論文開始突破西方中心論的歷史觀,提出新的觀點和看法,彰顯中國史學特色。當然,建構*的史學話語體系,任重而道遠,需要幾代人的努力。”
“公共之學術,只聞列邦之討論研究,往往闃然無吾族之跡,斯則邦家之奇恥大辱。”半個多世紀以前,前輩史家留下的深深遺憾一直縈繞在史學工作者的腦海。“今天,前賢所謂‘凡一國的文化,都應有民族的與國際的兩方面,每個民族必有所貢獻于世界,并有所獲于此世界’終于變成了現實,我們將從歷史和現實結合的角度把中國深厚的歷史文化和嶄新的發展面貌呈現給世界,讓‘中國話語’更加鏗鏘有力!”張海鵬如是說。 (本報記者 戶華為 周曉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