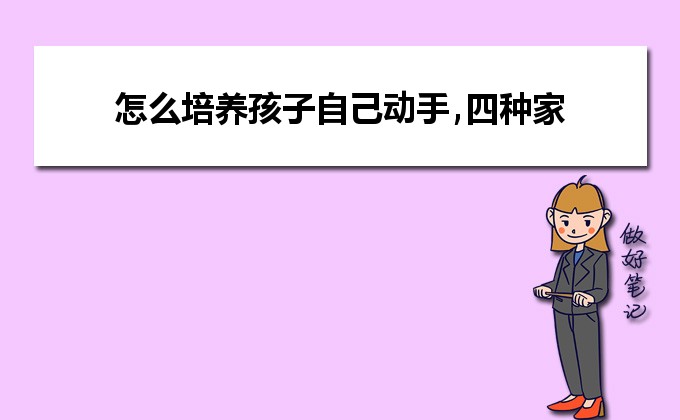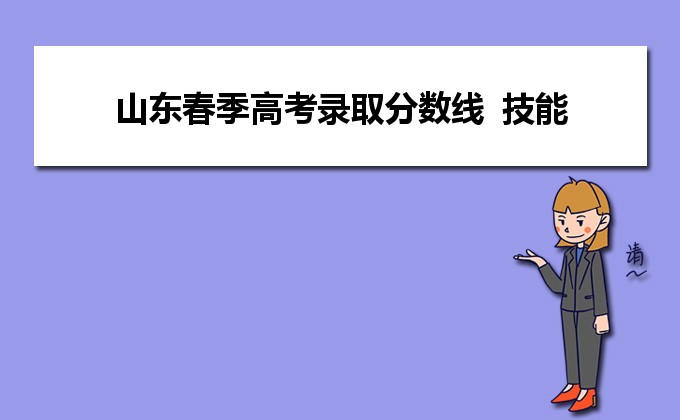在地球的任何角落,國家與教育的關(guān)系只能是國家任務(wù)決定教育發(fā)展,而不是相反。所以,不把國家大格局及其趨勢把握住,“教育危險論”難免成為危言聳聽。
■顧駿
最近網(wǎng)上傳播甚廣的《中國教育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一文,觸動了許多關(guān)心中國教育人士的痛點:宏觀上,中國經(jīng)濟騰飛,國勢日隆,急需世界級大師,而國內(nèi)盡管各類“人才”名目繁多,卻少有“頂尖”,以致每年別國發(fā)獎,國內(nèi)只聽到對教育的撻伐;微觀上,我們的很多學生,做題百般靈巧,體質(zhì)日趨下降,學習興趣淡薄,人格時有扭曲。這篇文章題目觸目驚心,教育種種不是也羅列了不少,但教育是否真到了“最危險的時候”?諸多不是真的都源于教育問題?似仍大有討論的余地。
就教育看教育,容易看得一無是處,但站在歷史的維度看教育,會讓人在批評之前,先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在中國社會的歷史轉(zhuǎn)型中,教育在滿足國家和民族重大需要上,承擔了什么職能?履行得如何?當下國家對教育的定位有否改變?教育能否順利實現(xiàn)轉(zhuǎn)變?這個轉(zhuǎn)變是否僅憑作者開出的“高校私立化,教育市場化”一個方子,就可以輕松完成?不把這些問題搞清楚,無論憂慮還是憤忿,其意固然可嘉,其方未必有效。
論證需要起點,必先確定一個各方共同認可的命題,方可展開討論。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整體是不斷進步的,這應該沒有疑義。現(xiàn)在的問題是,在社會大踏步前進中,教育有否發(fā)展,是否發(fā)揮了正面作用?回答應該是,也只能是。教育自身有發(fā)展,作用也很明顯,明眼人都有共識,否則論者難免掉入邏輯陷阱。如果在肯定社會整體進步時,認為教育竟然原地踏步,甚或落后了,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是不是有些自相矛盾?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堅持了一條原則,“發(fā)展就是硬道理”。經(jīng)歷了各種坎坷之后,國人認識到無謂爭論只會貽誤時機,要改變落后狀態(tài),只有專注于一個目標,即如何實現(xiàn)國家的最快發(fā)展,首先是經(jīng)濟的最快發(fā)展。
國家任務(wù)既定,教育定位也就明確了,只要有利于中國發(fā)展,特別是經(jīng)濟發(fā)展,就實現(xiàn)了階段性使命。站在這個基點上考察教育及其表現(xiàn),不難發(fā)現(xiàn),教育做得真還不錯。
改革開放的30多年中,中國完成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工業(yè)化和城市化的“兩位一體”。當制造業(yè)如錢塘江潮般成長的時候,社會對教育的首要要求是培養(yǎng)大量合格的技能型人才,而不是專注于基礎(chǔ)理論及其運用的諾貝爾獎候選人,雖然前者永遠不可能像后者那樣成為閃光燈的聚焦點,但中國成長中的產(chǎn)業(yè)體系和民生改善每一天都離不開他們。如果兩種產(chǎn)品都有,當然是好事。但要是教育暫時只能產(chǎn)出其中一類,那么,以加快發(fā)展為念的國家和民眾,肯定優(yōu)先選擇技術(shù)專家。教育的這一“工具”定位,無論教育的內(nèi)部人還是外部人,都無權(quán)也無力改變之。中國新增1500萬勞動人口,其中749萬是本科以上學歷畢業(yè)生。固然有人可以因為這么多大學生中找不出諾貝爾獎候選人而痛心疾首,但通過層層考試后接受了高等教育的畢業(yè)生,不會認為自己曾經(jīng)的努力完全是徒勞的。實際上,當中國經(jīng)濟還處于優(yōu)先考慮把產(chǎn)能做大,而不是做強的時候,教育專注于產(chǎn)出有助于提高GDP的“人力資源”類型和數(shù)量,是十分自然的。
至于將種種社會弊端都歸咎于教育尤其是“應試”的名下,那就形同“莫須有”了。個別大學生的極端行為如果僅僅因為發(fā)生于在校期間,就被認定為教育的責任,那遠比這多了去的極端行為因為發(fā)生在未能考上大學的青年人身上,是否又可以歸之于“大學拒絕接納他們”?貪腐的官員絕大多數(shù)大學畢業(yè),但腐敗是否又可以歸之于教育,而不是權(quán)力尚未被關(guān)進“制度的籠子”?如果任何人出了問題,都歸之于教育,豈非高估了教育的“魔力”?任何社會總有自己的問題,不能拿教育當解決一切問題的解藥。
毫無疑問,隨著中國經(jīng)濟和社會進入“新常態(tài)”,國家的目標正在調(diào)整,教育的職能也會調(diào)整。在地球的任何角落,國家與教育的關(guān)系只能是國家任務(wù)決定教育發(fā)展,而不是相反。所以,不把國家大格局及其趨勢把握住,“教育危險論”難免成為危言聳聽,“私立化”的方子也只能是膠柱鼓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