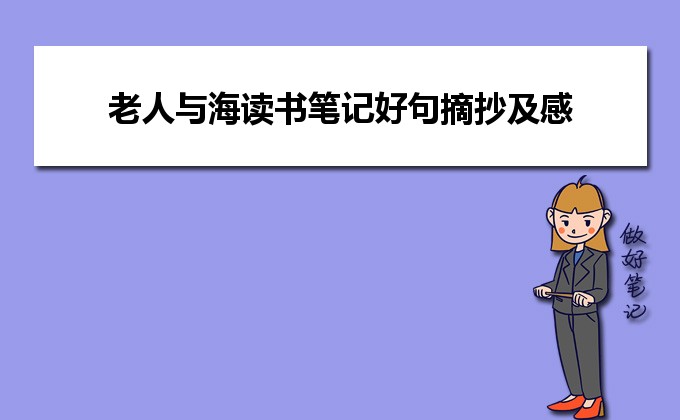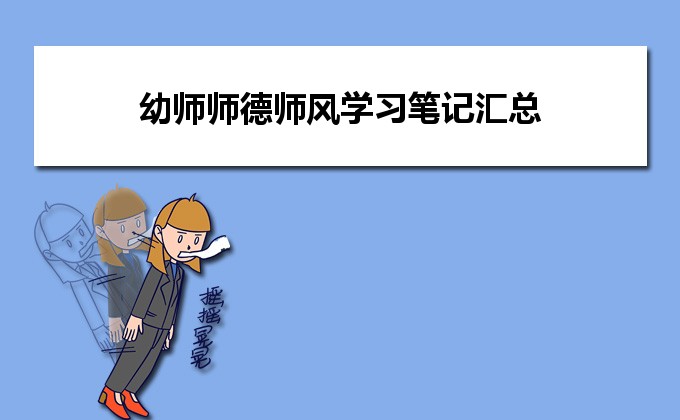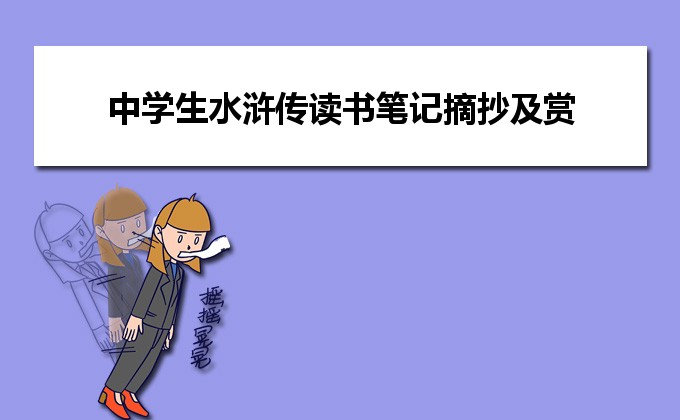所謂父女母子一場,只不過意味著,你和他的緣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斷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漸行漸遠(yuǎn)。你站立在小路的這一端,看著他逐漸消失在小路轉(zhuǎn)彎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訴你:不必追。 ——題記
“華安背著一個(gè)五顏六色的書包往前走,但是他不斷地回頭;好像穿越一條無邊無際的時(shí)空長河,他的視線和我凝望的眼光隔空交會(huì)。”將兒子第一次帶入校園,作者不知道如何形容自己的心情。看著兒子對(duì)這個(gè)陌生的地方的些許畏懼,她只能默默站在門口,在眾多的“彩色書包”中找出她的華安,然后以目光為兒子“踐行”。一句“我看著他瘦小的背影消失在門里。”結(jié)束了對(duì)第一次送別的描述,卻喚起了我腦海中似曾相識(shí)的畫面。那時(shí)的我同樣是被目送者,但是不同的是母親早早就告訴了我小學(xué)的故事。當(dāng)時(shí)我?guī)е裤健⑵诖约皩?duì)這素未謀面的小學(xué)的一絲畏懼,走進(jìn)了那扇現(xiàn)在看起來是那么親切的校門。我也曾無數(shù)次得回頭,但是迎接我的是母親的微笑。母親早早就告訴我說,“她會(huì)一直站在門口等我進(jìn)教室的。”所以那天,記憶中沒有眼淚,有的是和小朋友愉快的相處,老師溫柔的囑咐……
隨著第一次送別的結(jié)束,時(shí)間也來到了華安16歲的時(shí)候,這次的送別場地變?yōu)榱藱C(jī)場。“他在長長的行列里,等候護(hù)照檢驗(yàn);我就站在外面,用眼睛跟著他的背影一寸一寸往前挪。終于輪到他,在海關(guān)窗口停留片刻,然后拿回護(hù)照,閃入一扇門,倏乎不見。”同樣是離別,同樣是目送,不過這一次沒有當(dāng)年的“無數(shù)次回頭”,就連最后消失前的一瞥也沒有。不知是華安長大了還是他已習(xí)慣了離別,但知道的是作者心中充斥著無盡的失落。離別可怕嗎?或許有人覺得習(xí)慣離別才可怕。身居寄宿制學(xué)校已久的我早就習(xí)慣了與母親的離別,再加上當(dāng)年的叛逆。每當(dāng)我要走上校車再次與母親離別時(shí),都只是淡淡得留下一句“再見”然后就毫不猶疑地走上車。坐在窗邊看著窗外發(fā)呆,卻總能看到母親依舊站在路邊,她依舊笑著看著我,和當(dāng)年一模一樣的笑容。微笑消融了心中的冷漠而冷漠卻融化成了愧疚,滿滿得被裝入心中。
“現(xiàn)在他二十一歲,上的大學(xué),正好是我教課的大學(xué)。但即使是同路,他也不愿搭我的車。即使同車,他戴上耳機(jī)──只有一個(gè)人能聽的音樂,是一扇緊閉的門。”習(xí)慣了離別的華安已經(jīng)把自己關(guān)在了屬于自己的世界,聽著“只有一個(gè)人能聽的音樂”就這樣把他的母親關(guān)在了那扇緊閉的“門”外。我也不知道何時(shí)也在自己心中建起了這樣一扇門,只是總聽著母親抱怨,“當(dāng)年的兒子跑到哪里去了呢?”我只能苦笑:“我也不知道,說不定迷路了。”叛逆的棱角也隨著時(shí)間的消磨已經(jīng)慢慢褪去了,但是始終不變的是母親的微笑。每天早晨下車關(guān)上門時(shí),透過窗看到的仍然是那樣的微笑,十幾年依舊不變的微笑,直到我走進(jìn)校門,汽車才揚(yáng)長而去。
的確,長大的我早就不需像當(dāng)初一樣被母親牽著手走,所以母親看到更多的是我離去的背影,雖然我并沒有用背影告訴母親“不必追”。不置可否的是母親也追不上這個(gè)背影了,因此母親從一開始便選擇微笑看著我離開,就像當(dāng)年她笑著承諾:“進(jìn)去吧,媽媽會(huì)一直在門口等著你進(jìn)教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