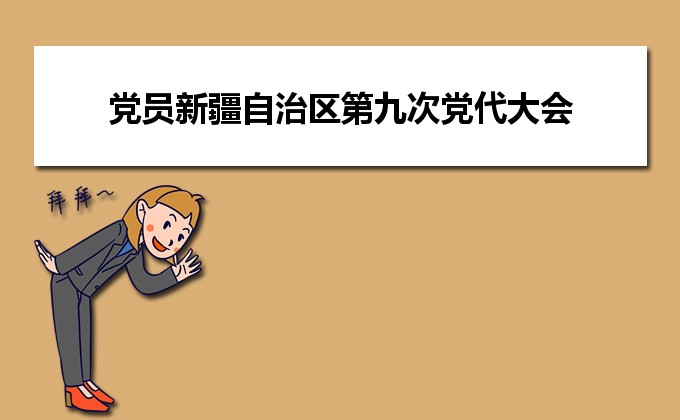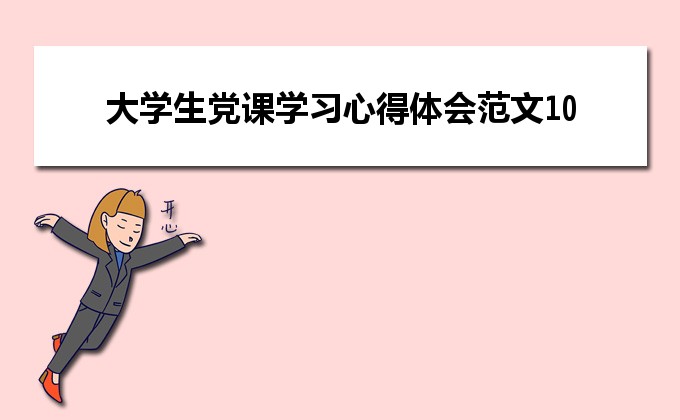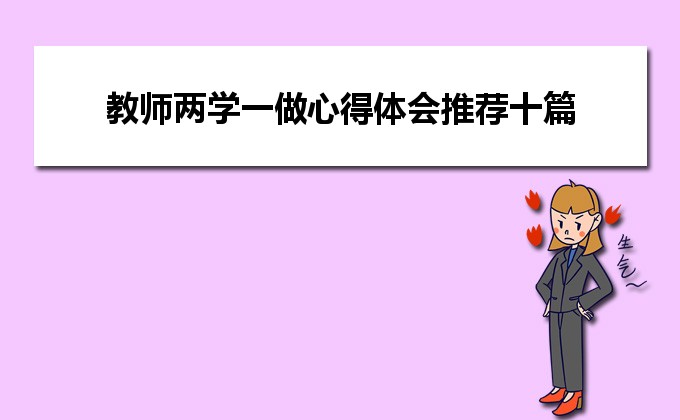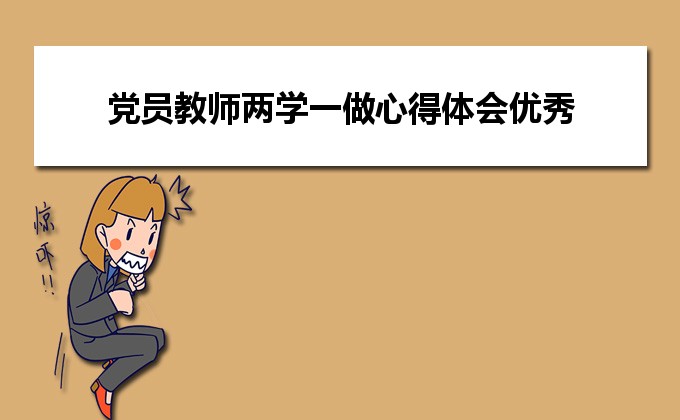路遙的中篇小說《人生》轟動了整個文壇的時候,有位詩人寫了以《致路遙》為題的詩作,高度表達了對路遙的敬畏。其中有這樣的句子:
第一次造山運動
挺立在黃河洶涌的臂彎
你同月亮一起升高
又躍上太陽穿刺重圍的黑暗
陜北民歌飄逸豪放的任性
交響樂朦朧而抽象的內涵
母親的呼喚和幼兒的淚眼
饑餓的鄉童和補丁滿身的老農
蚯蚓在不停地蠕動
愉快地死去又痛苦地復活
創造彎彎曲曲的歷史
永生的天才在沒有道路的道路上
走向沒有終點的終點
對于我們所處的這個現實社會,就是再激烈的批評,也是一種愛心的閃現,就像一個醫生對他的病人一樣,必須診斷準確,并且說出事實的真相,才可能對癥下藥,鏟除病根,使病人恢復健康。
路遙在中篇小說《驚心動魄的一幕》里,是這樣評價“文化大革命”的:“既是立法的議會,又是執權的政府,這是一些膽大而激烈的人物,革命的暴風雨剛席卷過社會,他們就露出了頭角,站在這場革命的前列沖沖殺殺。他們的性格特點如果能打比方的話,可以這樣說,要蓋一座房子,他們也許都是些笨蛋;如果要拆一座房子,他們會比誰都拆得又爛又迅速。”路遙的深刻,常常讓人驚訝,他的收獲一定是來自他那顆哲學的頭腦。在“文化大革命”那樣大動蕩的歲月里,人們就是這樣肯定著自己和否定著自己,在靈魂的大搏斗中成長或者墮落,都是瞬間的事情。路遙深知一個為真理獻身的人是偉大的,也是一種大愛,他贊美為正義挺身而出的英雄的同時,將自己也譜寫成了英雄。英雄就是敢于把頭顱獻上祭壇的人,讓人類來收獲他的智慧,讓歷史收獲它的精神。
路遙寫《人生》反復修改了三年,前兩次都因為不滿意而撕碎了,直到1978年才完成。當時他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不分晝夜,渾身就像燃起大火,口舌生瘡,大小便不暢,常常因為寫作,一個人在深夜里轉圈兒。我們知道,如果說收獲的話,路遙的收獲來自他高尚的認識能力和崇高的目標,以及超越常人的吃苦精神和犧牲精神。
路遙創作的準備工作以及精細的謀篇布局,在目前作家中無人能與之相比,路遙給中國文學創造樹立了一個典范,《人生》的價值,就是把當時好人壞人臉譜化的程式徹底顛覆。把人性的多面性展示出來,使人物描寫走出單一的格式化。把當時社會條件下青年人存在的問題和尖銳的矛盾,第一次擺到了人們面前。
當然一百個作家就有一百種寫法,但不可能一百種寫法都是最好的,最好的往往是能夠代表大多數人立場的作品,它既是本民族的,也是其它民族的,也是世界人民的共同心聲;它可能是現實主義寫法,也可能是后現代主義寫法或者是其它什么主義,但有一點是必須的,一切主義都是從現實主義或者叫現實的生活中產生的。就好像所有的莊稼都生長在大地上一樣。路遙是現實主義作家,但他的思想更多地反映出了現代主義的藝術光芒。
若要讓一個祖國強大起來,就是要讓每一個個體覺醒。路遙的小說并沒有空洞地去描述無邊無際空泛的大道理,而是始終關注和鼓勵個體的追求。如果每一個人都在追求真理,每一個人都在改變原有的生活條件,每一個人都在富裕和文明,那么這個國家就會迅速地改變。
路遙總是以活生生的人物形象說話,在具體的事件中展示真善美,在他的筆下沒有絕對的壞人,這些人的語言和行為總是在一定的社會環境下展開。路遙的創作決不脫離現實,總是活靈活現地反映生活中的真實,并且把他們上升到藝術的典型化之中。《人生》的成功,在當時已經遠遠地超越了當代中國文學,它帶著生活的氣息走進校園,走進知識界,走進工廠和農村,走進每一個讀者的心。
對于路遙的文學成就,以及路遙這個人,我們不能就事論事,你喜歡他,他也不可能是你的;陜北人喜歡他,他也不是陜北的;中國人喜歡他,他也不全是中國的,他應該是世界的。任何一種文化現象擴大到一種社會現象時,它的本質就產生巨變。任何一種地域化的解釋都是弱小的,甚至是無力的。
在俄譯本《人生》后記里,謝曼諾夫這樣寫道:“我看到過根據路遙小說改編的電影,這部電影在世界各國放映,電影是感人的和富有特色的。最后,我在中國和作家路遙本人會見了,他是一位純樸的,同時又是一個聰明的,善于思索的人。他已經是陜西作家協會的副主席。”是的,路遙一路走來,確實艱難,但是他創造的輝煌也是一個可觀的高度,這個高度又是用思想的積累凝結而成。這位外國友人敏銳地發現路遙作品里的精神內涵,路遙的另一個重要思想,就是“民族的根首先在農村”。路遙認識事物本質的能力是超前的,他認為“一個人就是一個世界,這個世界,不是孤立的,是和整個社會密切相關的、互相折射的,有些作品盡可以編造許多動人的故事,但它們沒有關注人物的精神世界,如果人在作品中只是一個道具,作品就不會深刻。歐洲有些作家,包括大仲馬為什么比巴爾扎克、托爾斯泰低一籌,原因就在于此”。
我們每一個人都想看到更多的天空,踏上更多的土地,而心靈的寬廣也許對一個正直的人而言會更重要,路遙比別人獲得了更多的珍寶。雖然路遙物質并不豐富,就算他一個人脫貧了,而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呢?就算他的家族脫貧了,而那個廣闊的黃土高原呢?路遙多年來心靈的負擔正在于此,他沒有只想自己,他想到的是一個陜北,一個貧民階層,一個民族最基本的生存狀態出現的重大問題,在陜北十年九旱的現實生活中,不是誰能在一夜之間改變了的,而更大的問題是,我們的態度、方向、意志和情感的衰竭。人從本質上講就是歷史,但把握現實的創造,解決現實的生存能力永遠是問題的關鍵。如果盲目地崇拜現實也是會犯錯誤的,我們的一些作家就是犯了這個錯誤,既不了解歷史,又不懂得現實,那肯定是沒有未來的,未來是歷史和現實準確判斷的結合,才能有正確的決策,贏得未來的成功。路遙的創作觀念有很多珍貴的東西,其中超越土地和農業,崇尚科學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農村的現實和他的理想之間的差距,常常壓得他喘不過氣來。
整個20世紀的中國,前半個世紀在戰爭中度過,而后半個世紀前半程基本搞了政治運動,經濟上貧窮落后,人民受盡苦難。路遙的創作思想,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形成并且成熟起來的。路遙一直尋找自由的空氣、自由的空間、自由的精神,但遺憾的是,自由的土地在哪里?路遙是一個富有開拓性和創造性的作家。他熱愛土地,贊美勞動,但永遠詛咒貧窮落后,他在小說《人生》里讓高加林說出他自己想說的話:當他的戀人黃亞萍問:“你想不想去?”高加林不假思索地說:“我聯合國都想去!”路遙對新思想,對現代化、對科技革命充滿了希望。一切外部世界的變化都在他的視野之中,并且在作品中有重要反映。
1988年,臺灣作家柏楊先生來西安,他就是著作等身,并寫出《丑陋的中國人》的作者。路遙代表陜西省作協與柏楊先生和他的夫人詩人張香華女士會面。他們的會面留有照片,不知道這兩位同樣有著深厚思想的作家談了些什么?但他們都太愛國了。一個以雜文為武器鞭撻丑惡。一個以小說作為武器批判現實。他們都是努力將命運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人,而不是被別人掌控或玩弄。